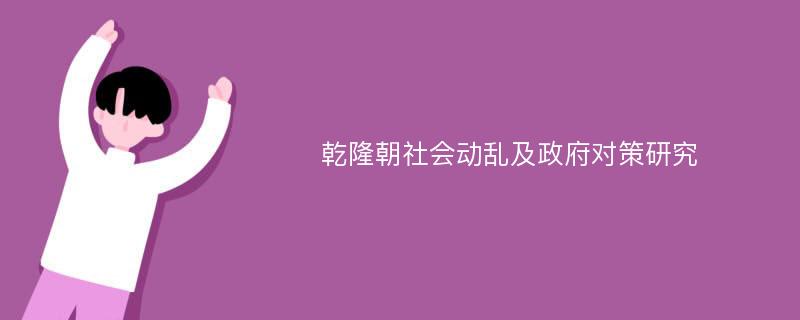
张佐良[1]2003年在《乾隆朝社会动乱及政府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乾隆朝是康乾盛世的顶峰,繁荣的表象下面是民众运动的潜流。乾隆朝社会动乱的爆发有其深刻地历史与现实原因。针对频发的社会动乱,清政府制定了种种对策予以镇压和平定。无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还是从现在研究角度来看,这些对策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主要表现在乾隆时期社会动乱仅限于局部地区,多数被消弥在萌芽之中,或在极短时间内即被平定。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统治在此后又延续了百余年之久。 本文主要探讨了清政府对社会动乱的预防、平定、善后等一系列对策及其演变规律,特别是关于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打击以邪教为首的秘密社会,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等相关对策,并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高度提出政策建议,探究其效用性和可实施性,以期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主要内容有:引言,界定社会动乱和政府对策的概念,追述前人研究成果,介绍相关史料来源;第一章,分析乾隆朝的社会背景;第二章,对乾隆朝主要社会动乱及秘密社会活动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探究其发展规律和趋势,并着重分析秘密社会在社会动乱中所起的作用;第叁章,通过叁个个案对比研究,探讨清政府在不同时期平定社会动乱的主要对策及其演变;第四章,对乾隆朝社会动乱政府对策进行总结性概括和评价,包括稳定社会基础、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对秘密社会特别是邪教的镇压、临变对策、善后措施、对清政府对策的相关评价等七个部分;余论,主要阐述主流意识形态对转型期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政治腐败与盛衰之变的关系及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社会动乱进行分类研究,利用计量史学、社会失范和社会控制基本理论对乾隆朝社会动乱作定量、定性及趋势分析,注重以第一手原始史料和充分的数据来说明问题。
骆源[2]2018年在《失序与重塑:咸同时期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动乱与乡村治理》文中研究指明清水江流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经济利益,在明清之际受到了统治者的极大重视,随着中央王朝在后期的开发治理过程中,该区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王朝政府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把清水江流域完全“内地化”。在明代设立土司、军屯等政策的基层上,清代又加紧了“开辟新疆”的步伐,通过改土归流和建置“新疆六厅”,希图把王权制度嵌入到清水江流域基层社会。在王朝政府的步步紧逼之下,由于未能考虑到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治理机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而强行在基层设置自己的统治机构。一系列不当的措施在基层逐步蔓延开来,造成了官员横征暴敛、官吏敲诈勒索、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的混乱局面,使得清水江流域的广大苗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在咸同时期之前,清水江流域就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苗民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清政府并未真正认识到如何合理的治理乡村基层,而一直加强行政、军事等方面的部署,目的是为了防止清水江流域苗民复叛。到了清朝后期,由于王朝政府日益腐败无能,地方官员更是肆无忌惮,在基层社会中横行乡里,祸害百姓,严重损害了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和生活秩序,广大苗民为了维护权益纷纷组织武装起义,发动了清水江流域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动乱——咸同兵燹。咸同兵燹的爆发彻底暴露了中央政府在基层统治的无能,地方清兵无力对抗咸同苗民起义军,乡村基层不得不自发组织武装保卫家乡。在咸同动乱的浪潮下,清政府无暇顾及清水江流域的治理,只得依靠乡村有功名与威望的士绅,于是士绅在基层的地位就显得极为重要,成为连接政府与乡村基层的桥梁。在政府与地方发生利益冲突之际,士绅便会与政府达成利益的基点,既无损于中央,又得益于地方。士绅组建的团练,取代保甲,成为治理乡村的新机制。在咸同动乱之际,不但肩负起抵抗动乱的职责,更是担当了制定乡规民约合法治理乡村以及维护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重任。士绅与团练,在清水江流域的乡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清水江流域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余华[3]2016年在《清中前期云南边防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古代,边疆防务对于国家统治者维护边疆稳定,巩固自身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备边着戍,国之重事”也,边疆不稳则国家不稳。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民族众多,地理环境复杂,对于构建边防体系有着重大影响。清中前期在云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清中前期边防体系的构建影响深远,持续至今,它不但是中国传统边防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是向近现代边防转变的基础。顺治、康熙、雍正时期(1660—1735年)是云南边防体系初步确立的时期。乾隆时期(1735—1796年)是云南边防体系的调整时期。嘉庆、道光时期(1796—1850年)是云南边防体系转变时期。清中前期云南边防呈现出向边疆土司地区推进的趋势。古代边防之防分为“外防”与“内防”,雍正、乾隆、嘉庆叁朝边防各有其特点:雍正朝镇压普洱土司起义、以及出兵西藏属于“内防”,乾隆朝中缅边境的冬防、中越边境防范沙匪、出兵越南属于“外防”,嘉庆朝则是“内外防”结合,既要防御“边外野夷”,又要镇压边境地区的民族反抗。清中前期云南边境管理的内容涉及缉私、流民管理、归附人员安插、治安、巡察等内容。清中前期云南军饷主要来源于地丁银,捐补、捐纳、羡余、铜息与铜钱搭银、生息银等在特定时期对云南军饷具有补充作用。军费支出主要包括制造兵器、衣甲、火药;修造军事工程;军粮主要来源于屯田收粮、征粮折色、购买存贮叁个方面。
白林文[4]2016年在《清代贵州“苗疆六厅”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贵州黔东南苗疆从雍正“改土归流”以后正式归入“王化”的“版图”。从开辟以前“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社会状况进入到设置郡县派遣流官治理时期,苗疆从间接统治过渡到了直接统治的时代。相对于几年的开辟苗疆来讲,100多年苗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长期治理更是清代面临的主要问题。前人对苗疆研究成果已不少,但主要侧重于经济开发、政治统治、法律调控以及苗汉文明互动等,纵向上没有把有清一代苗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一个全面总结,横向上也仅对某个问题进行单方面阐述,没有全面揭示苗疆“归流”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清代治理政策之间的重要关联。清代苗疆治理是一个不断调整、变动、发展的动态过程,反映了朝廷对民族地区治理政策日渐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本文围绕清代苗疆开辟的时代背景,雍乾和咸同两次苗民起事与清廷治理政策的关系,中央治理政策调整与苗疆社会发展状况的互动,“因俗而治”与加强中央控制等既矛盾又统一的问题进行叙述,通过分析清代前中期与后期治理苗疆的不同举措进行比较,从而揭示清代治理苗疆的重要邅变历程,指出清末苗疆治理的重要改革从而结束了苗疆动乱的历史。研究清代苗疆治理的历程和特点不仅可以总结清代治理民族地区政策的得失,也对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施政有重要借鉴意义。叙论部分提出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及前人对贵州苗疆研究文献的综述,指出苗疆治理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与存在的不足,并对相关的重要概念进行诠释。第一章总述改土归流以前苗疆的社会制度概况,如“鼓社”制度调整苗民的宗族关系,“理老”制度维持苗疆村寨的重要支柱,“议榔”组织调整苗疆区域。并简要对明代黔东南苗疆政治社会进行概述。此章为开辟苗疆的论述进行铺垫,也是全篇论文写作的前奏。第二章论述雍正对西南改土归流的重要历史时代背景及其目的以及开辟苗疆的历史过程。文章论述了西南土司制度发展到清代,与大一统政治思想日益冲突,清代为加强对西南交通、经济贸易和国防调整等重要战略的直接控制,在鄂尔泰的建议下进行了历史上着名的“改土归流”。“开辟”黔东南苗疆被纳入改土归流的重要一环。雍正用武力开辟苗疆后,来不及考察苗疆传统社会状况,对苗民直接征收赋税,从而导致雍正晚年爆发了苗民起事。乾隆上台后用张广泗为经理苗疆大臣迅速平定苗疆,从而为乾隆时期苗疆的各项稳健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叁章论述雍正乾隆时期苗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秩序的总体治理及成效。政治治理上,雍正开辟苗疆后,首先在苗疆建置“新疆六厅”,军事上在苗疆设营置汛,乾隆时期实行屯田制度,雍正和乾隆鉴于苗疆社会的分散和固有的传统社会习惯机制而采取了较灵活治理措施,在本无土司的苗疆建立了土司制度。乾隆时期苗疆社会治理主要是加大对苗疆基层的调整,对“生苗”“熟苗”采取分治,在基层设立苗寨“头人”制度,苗头隶属于土司,土司又隶属于流官,通过土司分管各苗山寨,借此流官从而统治苗疆社会。在苗疆法制文化风俗治理构建上,乾隆鉴于苗民固有的习惯法传统,规定苗人内部纠纷适用“苗例”仲裁。文化教育建设上,雍正时期就开始在苗疆建设学校,作为化导苗民的一项治理政策来施行。但是乾隆十六年以后考虑到苗民普遍识字会危及清廷的统治,取消了苗疆地区的社学,义学也日渐衰落。经济治理构建上鉴于苗民长期无纳税的传统,乾隆元年下令“永不征收苗赋”,从而促进了苗疆的经济发展;乾隆时期大力发展苗疆交通建设,开浚苗疆水道,建设苗疆驿铺,发展苗疆贸易,并移民开发苗疆,从而使苗疆的治理迈向了内地化的进程。乾隆对苗疆治理能适度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治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政策,如限制汉民移入苗疆,规定汉、苗不能交往,取消苗民接受文化教育、苗疆土地不断落入汉民手中而难以调整等,诸种矛盾错综复杂,从而埋下了嘉道时期严重的社会矛盾。第四章论述嘉庆道光时期苗疆各项社会矛盾的日渐突出。首先是“客民”不断涌入苗疆,苗民土地不断丧失,官、民的高利贷使苗民日益破产,从而伏下了深层次的矛盾。其次是苗疆屯政日益废驰,屯军不断挤压苗民的生存空间,而且苗疆驻地军队的采买制度日久生弊,逐渐演变成了盘剥苗民的一项弊政。鸦片战争以后,厘税在苗疆的推行以及徭役的加重也使苗民生活日益陷入贫困的境地。再加上苗疆土司通事等不断欺凌剥削苗民,官府在政治上与军事上也给苗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族群文化上,从乾隆时期不断移民苗疆的“客户”,至道光以后苗、汉“主客”地位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苗、汉文化差异日益成为族群矛盾的焦点。再加上清代后期苗疆人口不断增长,但土地却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使苗疆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第五章在第四章矛盾发展的基础上简要叙述了苗疆咸同动乱的原因、过程与结果。同治末年,苗民动乱被平定以后,官民经过战争的洗礼,对治理苗疆各项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苗疆社会各项弊政提出了改革措施。加上咸同动乱以后,苗疆社会阶层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基层地方士绅势力不断上升,为清末贵州苗疆治理的近代化治理重构奠定了下层基础。第六章是本文重点,论述咸同动乱以后苗疆近代化治理的重构。本章主要指出经过了近20年的咸同动乱以后,地方官府与清廷治理苗疆已体现了改革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治理构建上:一是逐渐废除“苗疆六厅”土司,从而减轻了苗疆基层苗民的负担;二是苗疆军伍开始向苗民开放,使得苗民第一次有了进入上层体制的窗口,突破了从前“以汉治苗”的樊篱,构建了“以苗治苗”的务实政治治理体系。经济治理重构上:在兼顾各阶层利益基础上规范了苗疆经济与赋税制度,一是坚决废除苗疆陋规,直接向苗民征收固定赋税,从而避免苗民长期受陋规的任意剥削;二是光绪初年朝廷规定“开垦纳赋占田制”,使苗疆土地所有权直接归入民、苗个体家庭,促进了苗疆乱后的经济得以恢复;叁是改革了苗疆屯田制度,把屯田逐渐收归地方流官管理,同时取消驻扎苗疆军队的“采买”制度,使苗民生存压力逐渐减轻。文化习俗治理构建上:一是在苗疆大力发展教育,广泛普遍建设学校,苗民从此得以进入学校学习汉语文化,使苗疆文化教育迈入了近代化的重构;二是地方官在政治实践中已体会到民族地区“因俗而治”的传统政治思想重要性,在相对尊重苗民风俗的基础上推行“汉化”政策,从而避免了苗、汉关系的紧张。社会基层的治理构建上:一是通过官府的承认从而提升苗疆地域习惯法以代表正统的国家权威,并以石碑刊刻的方式广泛公布于苗疆基层村寨,晓示地方官员、土弁以及苗民,既适合了苗民的传统习惯,也使国家法制顺利扩张深入苗疆基层;二是在苗疆土官式微之后,地方士绅不断崛起的情况下,朝廷开始在苗疆建立了保甲制度,把苗疆原来流官-土司-苗寨头人-苗民的社会治理结构,过渡到流官-保-甲-苗民的统治结构,从而使苗疆的国家化、内地化进程进一步加深,为苗疆近代化秩序重构奠定了基础;叁是面对苗疆村寨分散的特点,流官通过授权地方村寨进行“自治”,此种措施在减少治理成本的同时达到有效构建苗疆基层秩序的目的。结语在前面几章论述的基础上,总结清代苗疆治理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一是从国家政权治理角度上看,苗疆治理治理方式从族际主义治理向地域主义治理逐渐转型;二是从政府治理的方式上看,苗疆治理方式从一元治理逐渐向多元治理转型;叁是从治理的主体来看,从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苗疆转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苗疆地方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并存上来;四是从治理的性质上看,从防范控制苗疆苗转变到防范与注重苗疆民生的治理并存上来;五是从治理的对象上来看,已从开辟前的边疆治理政策转入了内地化治理模式上来。以上诸种具有改革性的治理措施使苗疆进入了近代化治理重构。
黄梅[5]2016年在《清代边疆地区“汉奸”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的变化为背景,提出“汉奸”治理成为清朝治边的重要任务,归纳了清朝统治者对“汉奸”危害的认识和治理“汉奸”的对策,并在此基础上对清代“汉奸”治策的得失进行分析,剖析了清代“汉奸”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的原因,并对“汉奸”词语在清代的使用特点做了分析,指出“汉奸”词语在鸦片战争前主要是一个用于边疆治理问题的词汇。雍正朝在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不法汉人为自身利益而教唆土司和苗民抵抗清政府的改土归流,边疆地区的汉奸问题开始显现。改土归流改变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外来汉民和新设流官政权对夷民的欺凌成为边疆地区的主要社会矛盾,导致了新的汉奸形式的出现。煽惑土司和苗夷的不法行为、盘剥土司和夷民财产、包揽和教唆诉讼、协助藩属国损害清政府利益和参与藩属国内部斗争,构成清代汉奸违法活动的主要形式。“汉奸”的一系列行为严重影响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引起了清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一是主使土司和苗民的不法行为,具体表现为主使土司抵制改土归流、挑起土司之间的争斗、充当苗人叛乱的策划者和教唆夷民烧杀抢劫。二是参与土司和苗民变乱,具体表现为参与土司的反叛斗争、充当苗民起义的参与者和追随者及为番民贩私和销赃。叁是侵占夷民和土司的田地。四是参与藩属国危害中国利益活动。五是进入藩属国为匪。汉奸直接主使和参与夷民反对中央政府斗争的行为,阻碍了清政府的边疆开发进程;汉奸侵占田产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夷民的生计,夷民为生存而被迫变乱,导致边疆地区经常性的动荡不安。清朝统治者将汉奸视为影响边疆地区安定的重要因素,制定了一系列打击和根除汉奸的措施。一是直接打击汉奸的对策,包括对汉奸严密缉拿和从重究拟、禁止汉民私往夷地、将稽查和捉拿汉奸列入土司与流官考成、对土司聘用主文和延幕进行严格控制及颁行保护夷民田地所有权和利益的措施。二是消除汉奸危害的产生的基础。清统治者认识到兵役的欺凌、夷民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生计困难是汉奸得以教唆和欺凌夷民的基础,制定了严惩官史和兵役欺压夷民的行为、以夷治夷、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停止将遣犯安置于偏远夷民聚集地区和推行多项保障少数民族生计的措施等政策来消除汉奸危害产生的根源。清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惩治和根除汉奸的措施,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夷民和土司利益的积极效果,在一定程度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但汉奸治理中一些关键措施的缺失,也使得汉奸问题在清代一直延续。清政府对生夷和生苗坚持不编户的原则,保甲制度的缺失导致地方官员无法彻底清查汉奸,为潜居苗疆和土司地区的“汉奸”保留了生存空间。对于土地侵占这一导致苗疆动乱的重要诱因,清政府主要通过民、苗隔离和划界等方式来解决,苗民的土地所有权未得到政府的确认,汉奸侵占苗民田产的行为得以长期持续。清政府于苗变后在苗疆大量安插屯军,授给良田,幸存的苗民只分得山头地角的贫瘠耕地。随着人口的增长,苗民人口数量与土地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苗民为生存而被迫起事,汉奸产生的基础条件被再度强化。清政府将民、苗隔离视为根除“汉奸”的主要治策,试图通过禁止民、苗杂居和通婚来断绝汉奸教唆和欺凌夷民的机会。民、苗隔离政策是把“双刃剑”,在保护夷民的同时,也阻碍了夷民学习内地生产技术和通过贸易来改善生活的途径,不利于消除生计困难这一汉奸得以教唆夷民的根源。“汉奸”一词中的汉并非专指汉人,也包括熟番、熟苗和熟夷等已编户的边疆民族,“内地民人”成为汉奸的必备身份条件,增加了清政府在汉奸认定和处置上的复杂性。清政府将强占和盘剥夷民田地的内地民人定为“汉奸”,但对这一类型汉奸的处置则是较宽松的,显示了清朝统治者开发边疆的积极态度。清政府认定和处置汉奸的法律依据不足,主要是依据清朝皇帝的主观判断,导致地方官员在汉奸认定和处置上混乱。边疆地区的持续动荡使得清统治者的汉奸治策出现了倒退和矛盾,对边疆民族由教化到愚民、由同化到隔离和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封禁,都体现了传统羁縻思想对解决“汉奸”的问题的制约。
王力[6]2010年在《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收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民族学的社会实地调查资料及政治学的政策分析法,系统论述了清朝在回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政策措施的渊源、背景、内容、特色、功能、演变、结果、得失及其影响;如政策制定的过程及其理念,不同时期政策调整的原因及其意义,朝廷和地方官员对回疆事件的决策、观点及其影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及其后果等等;动静并重,正反兼顾,力图全面、客观地把握有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的整体脉络,真实地反映其发展演变历程,并给予客观的评价。全文共包括导论及八章内容。其中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的选题缘由、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资料以及学术界对清代回疆治理政策的基本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了清朝统一新疆前对回疆地区的经营;这一时期,由于历史原因,清朝与回疆地区的接触较少,清朝的治理政策主要通过建立互动关系并以控制哈密、争夺吐鲁番的形式实现。第二章、第叁章论述了新疆统一至新疆建省时期清朝的回疆治理政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于回疆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之后,开始在回疆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实现全面治理;同治叁年(1864年),回疆地区爆发农民起义,清朝在当地的统治被冲垮,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窃据回疆部分地区十叁年;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收复新疆,设置行省;这一期间,回疆整体上处在军府制度统治之下,清朝的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及地域色彩。第四章论述了新疆建省后清朝回疆的新治理政策;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并逐步开始内地化,清朝回疆治理政策也进行了重大调整,推行郡县制度,实施新政;此时,清朝政府在回疆实施的各项政策开始与全国保持一致,并逐步与国际接轨,这加速了新疆的近代化进程。第五至第八章以专题形式分别论述了清政府在回疆地区的边防、经济、教育、宗教政策,探讨了各项政策实施的背景、过程及其特点和得失,以期从中吸取教训,获得有益启示。
吴飞[7]2012年在《清代平远客家人迁徙及对台湾的垦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政府实施“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有利人口增长的措施,以及农业文明的进步,清代粤东地区人口急剧加增。粤东民间形成较大规模地向四川、广西、台湾等地移民。各县在人口迁移方向、数量等方面上表现不同。一般认为,粤东地区“人地矛盾”是造成这种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人口迁徙是传统社会的一种常态,用一个区域内人口与土地之间矛盾作为人口迁徙原因显然过于笼统。本文研究粤闽赣叁省交界之处的一个山区小县——平远县,对其清代社会情况进行阐述,以人口迁徙为脉络探讨一个地域的客家社会变迁。在清代平远客家人迁徙各方向上,文章对平远人在台湾的垦殖作重点分析,探讨平远与台湾两地之间互动关系,从而展现一幅具有“总体史”意义的区域移民史画面,进而探讨迁徙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问题。透过分析当时国家政策,具体描述一个地域自然生态环境。将当时国家宏观环境与地域生态环境的综合分析,本文认为人口迁徙而非一概而言的“人地矛盾”所造成,更要关注的是迁徙背后的国家政策导向,最不能忽视的是国家力量的推动,其次是一个地域的生态环境,再者是移民个体主观因素。
张佐良[8]2007年在《18世纪中国秘密社会与社会变迁》文中提出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变革的前夜,表面繁华的康乾盛世即将隐去,秘密社会作为潜在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日益成为社会动乱最主要而有效的组织手段,使得清中期社会动乱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增长快的特点。由秘密社会发动的反清活动日渐升级,撼摇着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对此后中国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李贵彬[9]2009年在《清代乾隆时期人口问题及政府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史为鉴,可知兴亡。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叁亿人口的大国,众多的人口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回首过去,清代乾隆时期人口的剧增是今天庞大人口基数的历史基础,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清代乾隆时期人口剧增原因、影响及政府对策等叁章进行写作。第一章乾隆时期人口剧增的原因及情况。首先,分析了乾隆时期人口剧增的原因,其原因归纳为中国传统文化、高产作物的推广、政治局势稳定、户籍赋税制度改革、赈济政策的完善、气候因素影响及医疗技术发展等方面。其次,阐述清前中期及乾隆时期人口增长的情况。第二章人口过剩带来的压力及影响。首先,对人口增长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做了解读,认为在社会承受能力范围内的人口增加会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在社会承受能力范围外的人口过剩会阻碍、破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其次,分析了乾隆时期的人口攀上了历史巅峰所隐藏的严重社会危机,如人地矛盾加剧、物价上涨、财政体系受到冲击、人口大规模迁移、农民起义频发、吏治腐败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第叁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论述乾隆帝及其政府应对人口压力的对策。首先,介绍清朝前期统治阶级对于人口增长的认识,康雍乾叁位皇帝均感受到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其次,面对人口压力,乾隆帝及其政府采取了重视农业生产、解决粮食供给、组织向边疆移民和普免天下钱粮等应对政策。再次,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乾隆时期解决人口压力对策做了评价。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利用文献综合、图表、比较和归纳等研究方法,同时以调查、访谈、网络研讨作为补充方法。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史料的分析,梳理出史家极少探讨的乾隆时期应对人口压力的主要对策,并详细的论述了对策内容。在探求乾隆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状况、影响及政府对策时,总结得失,既展现了乾隆时期人口问题及对策的全貌,又为今天我国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借鉴。
金贤善(Kim, hyunsun)[10]2016年在《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疫灾”是疫病灾害的简称,疫病与环境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分析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疫灾疫灾流行概况、特点、原因。而两湖地区地貌类型复杂,不同地貌下的经济、人口方面存在差异,故该地区疫灾的流行具有区域差异的特点。因此拟将两湖地区的疫灾流行特点按照平丘地区和山岳地区分开研究。并试图以社会史的角度来论述政府(包括朝廷及地方官府)、地方势力(包括绅士、富户及慈善组织)和民众在疫灾爆发时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明清期间两湖地区疫灾十分频繁,平丘地区疫灾趋势在某段时期集中,如集中分布于1580、1640、1700、1720、1830年代,而山岳地区疫灾较平缓。明末1580、1640年代,平丘地区在“小冰期”影响下,气候变寒冷干燥,旱灾频发,从而发生严重疫灾。相反,清代1700、1720、1830年代,两湖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集中,加上平原地区的垸田开发和山岳地区的盲目开发,洪涝灾害频发,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疫灾。此外,通过分析个别年份的病种,1640年代鼠疫(bubonic plague)猖獗于华北地区,随后扩散至河北、河南、山东,甚至江南地区。根据疫病死亡率、鼠群的移动及死亡、气候与鼠蚤关系、李自成与张献忠起义的移动径路等来推断,在两湖平丘地区流行的疫灾很有可能是鼠疫。另外,关于1832年发生的疫灾,1820年代霍乱传入中国,并在1821年前后形成全国范围的流行(以江南地区和河北平原最为广泛),据当时贸易、水灾导致的状况及高死亡率,不能排除霍乱的可能性。总之,明清时期平丘地区的疫灾主要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而与中国其他地区又有密切的联系。与平丘地区相反,山岳地区地理环境因素对疫病流行的影响很大。因该区森林密布,“瘴气”盛行,为地方性疫病(如疟疾)的流行打下基础,而大规模的皇木采办及民众滥伐森林,则直接导致了疫病的流行。随着山林的不断开发,地方性疫病逐渐减少,但由于生态破坏,进入清代,水灾频发,从而导致的疫灾次数大大增加了。另外,山岳地区的盗寇侵犯、荆襄起义、苗族起义、张献忠与李自成农民军、王朝叛乱(吴叁桂、金声桓的反清活动)、白莲教起义等各种动乱持续不断。盗贼侵犯、动乱频繁,对于该地区疫病发生有深刻的影响。明清时期,该地区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与外界交流日益频繁,天花、霍乱这样的疫病开始传入,由此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的疫灾。总之,山岳地区的疫灾与地理环境、战乱及人口流动等因素有关。从对疫灾的应对来看,由于明清时期平丘与山岳地区之间疫灾成因不同,所以政府、社会力量和民众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已有研究已经表明明清两朝对疫灾采取比较消极的措施,但考虑到政府对一般水旱灾害采取比较积极的措施,而平丘地区的疫灾发生原因是水旱灾害,山岳地区则有所不同。另外,两湖平丘地区为全中国的“粮仓”,经济发达。因此,可以推测政府对两湖平原和山岳地区采取不同的态度,发生水旱灾害时对平丘地区赈灾更多,对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疫灾自然也有附加的防治效果。而且,地方绅士和一些社会组织都以各自的方式展开救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救助的不足,尤其是在官府对于基层社会的作用日益削弱的情况下,地方绅士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救济灾民的角色。另外,民众的对应方面,因为相同的时代的背景下,虽然与山岳地也有相似之处。平丘地区疫灾与自然灾害有关,自然信仰多。并且城隍信仰等官方认可的信仰非常普遍,或者通过对神灵崇拜的官方化,将民间祈神驱病等活动控制在官绅的主导之下。因此,平丘地区的许多民间信仰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持政府的统治有着极大的帮助。与之相对应,明清时期两湖山岳地区(尤其湘南地区),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瘴气之地”,存在着地域偏见与民族歧视的文化概念,经常将该区作为贬官之地。此外,由于地理特殊性和战乱的原因,这里经常爆发疫灾,但对政府而言,控制一个地区的稳定是最重要的,救灾则是其次,因此对山岳地区的疫灾非但几乎没有救助活动,疫灾流行反而会成为政府镇压战乱的机会。因此山岳地区不能经常得到政府的救济而无法采取合适的措施以应对疫病。而且地方官员及地方力量得救助也有限。没有救助情况下,山岳地区民间信仰非常盛行,尤其巫术崇拜广泛蔓延,而且民间宗教也利用巫术与疫灾夸张教势。反抗统治阶级的活动中常常借用迷信和巫术的手段,因此山岳地区的民间信仰不利于国家统治。
参考文献:
[1]. 乾隆朝社会动乱及政府对策研究[D]. 张佐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失序与重塑:咸同时期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动乱与乡村治理[D]. 骆源. 贵州大学. 2018
[3]. 清中前期云南边防研究[D]. 余华. 云南大学. 2016
[4]. 清代贵州“苗疆六厅”治理研究[D]. 白林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5]. 清代边疆地区“汉奸”问题研究[D]. 黄梅. 云南大学. 2016
[6]. 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D]. 王力. 兰州大学. 2010
[7]. 清代平远客家人迁徙及对台湾的垦殖研究[D]. 吴飞. 南昌大学. 2012
[8]. 18世纪中国秘密社会与社会变迁[J]. 张佐良. 菏泽学院学报. 2007
[9]. 清代乾隆时期人口问题及政府对策研究[D]. 李贵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09
[10]. 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D]. 金贤善(Kim, hyunsun).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乾隆论文; 苗疆论文; 雍正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清代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明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