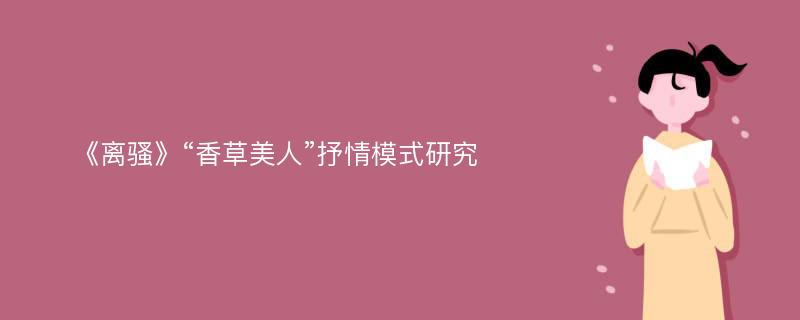
刘志宏[1]2003年在《《离骚》“香草美人”抒情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唐以来,对《离骚》“香草美人”的研究或遵循“以经解骚”之传统模式,而自近现代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文化背景研究兴起,各秉所长,可谓聚讼纷争。学者们依靠蓬勃发展的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等,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文本考据,力图全面、立体、纵深去重塑我们对《离骚》的诸多理解。然多作散点研究,取此放彼,难免有牵人就己之嫌。 本文叩其两端,认为“香草”和“美人”作为一个抒情表达模式的代表进入文学系统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其中凸现着人类最原始的行为和思维习惯以及历史形成的民风民俗。这些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并试图通过此指出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意义。 另,本文旨在通过原型研究方法,在传统“比兴”分析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作原型剖析,将其抒情模式分为两种,即“比兴模式”与“原型模式”,并进行了文化心理分析研究。亦属一管之见,冀于此领域研究有所裨益。
马迎春[2]2014年在《从符号—结构谈《离骚》和《神曲》的文学手法》文中认为《离骚》和《神曲》艺术特点研究,以及两个作品的比较研究都比较多,本文尝试运用符号-结构的方法,从文学手法叁个层级对两个作品艺术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借助符号-结构的方法有助于将研究有序化;同时本文运用实际数据描述文学事实,实证地揭示两部作品存在的文学现象;这不同于已有的不分层次、笼统的研究。《离骚》和《神曲》艺术特点不同,从文学手法看,首先是对文学手法诸类型自由组合运用的不同。这些类型分别是:最小文学手法的叙述、描写、抒情;整一文学手法的整一事件、整一意象;文本文学手法的题材、文体-体制、语体风格、结构布局和形象塑造。从文学手法选择组合考察看,两部作品都是主观超验性的作品,但《离骚》是在主观超验的总体架构之下具有浓厚的抒情性,体现了受到“比兴”传统影响的中国古代言志诗的特征;而《神曲》在主观超验的总体架构下呈现为客观的叙述、描写,体现了西方“模仿说”和中世纪“寓言说”双重影响下的中世纪意大利精神史诗的特征。两部作品的这种基本特征,本文将从叁大文学手法层级具体讨论。从最小文学手法看,《离骚》偏重使用叙述与抒情最小文学手法,《神曲》偏重使用叙述和描写最小文学手法。在《离骚》中,叙述和抒情分别占全文的39.6%和38.2%;描写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占全文的22.2%。《离骚》抒情大多位于前半部分,叙述大多位于后半部分。在《神曲》中,叙述和描写分别占总量的51.4%和44.3%;抒情最小文学手法使用则较少,仅占4.3%,远远低于《离骚》的38.2%;而《离骚》的描写是22.2%,也远远低于《神曲》的44.3%。从最小文学手法出发,我们还发现《离骚》运用了大量比兴-隐喻,这些比兴-隐喻构成了几个完整的系列;而《神曲》使用了众多的史诗明喻,这些史诗明喻不构成完整的系统。《神曲》还运用了大量的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典故-隐喻,而《离骚》没有运用正真意义上的典故。从整一文学手法看,《离骚》构成相对简单,有叁个层次;《神曲》构成则复杂一些,层次更多:有四个层次。从整一文学手法出发,我们还发现《离骚》和《神曲》的象征方式不同,《离骚》的象征比较简单,而《神曲》的象征比较复杂,是象征与寓言并重。《离骚》的象征,不管是局部象征还是整体象征,大都由最小文学手法的隐喻通过博喻的方式发展而来。《神曲》的象征分为两类:但丁个人化象征、基督教传统象征。在《神曲》中,除了象征,还有叁个层级的寓言,《离骚》没有寓言。从文本文学手法看,《离骚》和《神曲》结构布局、人物形象塑造不同。在结构布局上,《离骚》以诗人九死不悔情感为主线贯穿首尾,不注重叙述必然性情节,是一种主观淡化情节,体现了以抒情为主的结构原则;《神曲》则是以基督教趋善避恶道德律为准绳,组合运用线状结构与空间结构,体现了寓言结构布局原则。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离骚》将人物放置于“去与留”的矛盾冲突中,运用对比、直抒胸臆等多种艺术技巧突出人物的情感,塑造了情感强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神曲》则根据基督教的善恶观念将人物按类划分,人物具有寓言化的、类型化的特点。
纪晓建[3]2014年在《汉代楚辞学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楚辞学历时两千余载,以汉代楚辞学成就最高,也最具特色。汉代楚辞学是中国楚辞学的肇始,是中国两千余年楚辞研究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国楚辞学的巅峰。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以形式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成果的卓越性和权威性为后世历代楚辞学难望项背。从楚辞学发展史看,汉初宫廷楚声的兴起是汉代楚辞学的准备期;西汉前期是汉代楚辞学的创立期;西汉后期是汉代楚辞学的发展期;东汉前期是汉代楚辞学的转型期;东汉后期是汉代楚辞学的巅峰期。学术的演进往往以伟大学者的伟大成果问世为标志。在汉代四百余年的楚辞学史上,众多楚辞学名家以卓越的学术建树和独特的骚学风格推动汉代楚辞学的发展。汉初贾谊在屈原精神感召下创立骚体文学,开创了汉代乃至后世百代对屈原及楚辞一种特殊的接受形式;刘安以《离骚传》开楚辞章句训诂与义理阐释之先河,实现了汉代文人对楚辞从口诵、摹拟到章句训释和义理阐发的跨越,奠定了汉代楚辞学的基础;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最早也最全面地保存了屈原史料,揭橥了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骚怨精神;刘向完成了《楚辞》的最终编辑和命名;扬雄较早地认识到赋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具备有“铺张扬厉”、“侈丽宏衍”的独特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质,开后世楚辞美学批评之先河;班固突破了自汉初刘安《离骚传》开创的屈骚人格批评模式,充分肯定《离骚》的艺术成就,抓住了楚辞文学形式美的特征,表现出自觉的文学审美批评意识,标志着汉代楚辞学的正式转型;王逸的《楚辞章句》在吸收两汉传注体训诂长处的基础上,既博采众长又不囿旧说,在对楚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全面肯定的基础之上注重审美批评,对楚辞中纷繁复杂的文学意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审美阐释,成为汉代楚辞学集大成之作,造就了中国楚辞学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就汉代楚辞学的背景与特色而言,汉代学术思想融汇了先秦诸子各家各派的思想,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上的内圣外王和学术思想上的儒道合糅。汉代知识分子直承春秋战国时期文士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同时在汉代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体制下,又不得不养成“明哲保身、全身远祸”的心态特征,从而造就了他们亦儒亦道、亦进亦退、与时变化的心态结构。因此,“依诗释骚”和“儒道杂糅”这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学术特征和文人心态在两汉楚辞学领域“和谐”地并存着。儒家价值观成为汉代楚辞学者评价屈原人格及其作品的标准,而道家思想又在潜移默化中支配着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判,正是这种儒道思想的交融和矛盾斗争,推动了汉代楚辞学的发展。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对汉代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汉代文学的滋润,这种影响是巨大而深透的,两汉四百年的文学可以说是在楚辞光辉的照耀下发展和壮大的。楚辞的思想和风格决定着汉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带动了新文体的产生。楚辞从形式到思想内容都成为汉代文人争相模拟和仿效的对象,因此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骚体文学。骚体文学是楚辞的衍生物,无论是体制内容、艺术风格还是抒情言志特色都深深地烙上了楚辞的痕迹;汉代乐府诗是在楚骚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文人五言诗和七言诗在抒情和表达技巧上也深受楚辞的影响;建安诗歌中慷慨任气、直面人生风格特征更是对屈原作品强烈入世精神的直接继承。楚辞对汉赋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汉赋创作的范本和准的。汉赋在体制形式和表现方法上都和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汉代骚体赋不仅形式上接受楚辞的体式,而且在思想内容和抒情方式上也继了楚辞的传统,并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汉大赋中排比铺陈的艺术表现方法和铺张扬厉的语言风格也与楚辞密切相关;楚辞抒发“怨情”的特色为汉代抒情小赋所继承;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和“咏物写怀”的比兴特色为汉赋所借鉴。
罗建新[4]2010年在《楚辞意象之构成考论》文中提出作为诗歌之本体的意象实际上包涵了四个组成要素:属于意层面的情与理和属于象层面的物与事,而所谓“意象构成”即是此四要素相互发生关系,生成文本形态的单一意象与复合意象的过程。基于此种认知,可以认为,“楚辞意象构成”这一论题主要包括取象、寄意、象与意的契合以及文本中的意象安置、组合等层面的内容。总体而言,“楚辞”作者所取之象可划分为物象与事象两大类型。其中,物象又包括自然物象与人工物象,前者指相对于主体之外的客观物,主要有动植物、地理天文、季候时节等,后者指属于人的及与人发生关联之物,主要有性别、器官、生理特点、疾病、衣饰、器物及社会角色等;而事象则包括实存事象与虚拟事象,前者指天地间的实存事,主要有历史事象与现实事象;后者指主体所虚拟想象之物事,主要有神灵鬼怪、灵禽瑞兽及登天神游诸事。“楚辞”所取之象沾染了浓郁的南楚地域文化色彩,其范畴较为丰富广阔,且具有鲜明的虚拟想象性特征。这些特征的出现与南土地理环境、楚文化特征、战国之际南北文化融合的时代背景及楚人审美心理与创作主体个人修养等因素有关。身处战国末世的“楚辞”作者,为抒泄个体之忧愁烦郁,常将诸多情与理寄寓象中,以自明与自救。就具体文本而言,其所寄予之情主要有慕清自守之绪、生逢国衰之忧、激愤不平之怨、忠贞不渝之情等,而所寓之理则主要有从历史文化中汲取的经验如历史鉴戒观念、历史发展思想及其在个体人生经历中所总结处的某些规律、认知、哲理等。为准确地传递出这些意,“楚辞”作者采取了直抒其意与讬象寓意两种方式来设置篇题,安排文辞。倘若以格式塔心理学派之观点为参照,当可见出,“楚辞”作者所取之象与所寄之意是借助于“异质同构”的心理认同而发生契合的。亦即,在创作准备阶段,象本身具有某种特征,这些特征能让人产生出不同的情感体验或理性认知,尽管这种体验或认知本是发生在人大脑皮质中的生理现象,但在主体心理认知领域中却被体验为是象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如此一来,象与意便借助于大脑皮层的反应这一媒介,以“相似”的心理体验而发生契合。在“楚辞”中,象与意的契合形态可分为象之形貌与主体情感体验、象之形貌与主体理性认知、象之性质与主体情感体验、象之性质与主体理性认知相契合等四种类型。当然,因作者、读者审美体验之差别与意象本身所具有的浑融性特征,这种区分实际上是相对而言的。从文艺心理学角度看,实现象、意契合的主要媒介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联想思维。亦即,象能让主体衍生出诸多联想,如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等,而这些联想能在审美视域中与主体所欲寄托之意相契合,从而沟通象、意,并经由创作主体之艺术加工而生成审美意象。在生成观念中的“意中之象”后,“楚辞”作者对其进行了安置经营工作,这主要体现在意象位置与意象组合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其可据传递旨意之需,于文本的篇首、篇腹、篇尾诸部分自由安置意象,这在体制上标志着中国诗歌之独立;就后者而言,其组合意象之方式可划分为并置式、归纳式、演绎式等叁种主要类型,在每种类型中,“楚辞”作者有意识按照特定的逻辑关系,或迭用,或交替,对之进行多样、立体组合,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意象体系。从“意象构成”角度看,“楚辞”之于中国诗歌而言当具有转型意义。其拓展了取象范畴,开阔了创作主体的审美视野,提供了借助于诗歌来寄寓主体复杂多样的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的可能性,使得中国诗歌能够在题材、主题、类型的多样性上能有着更大的发展。不仅如此,“楚辞”作者之创作目的及创作实践皆表明其是自觉创作而非自发吟唱,这就标志着文学自发阶段的结束及其感性自觉阶段的开端。“楚辞”作者的这种主观、能动的文学创作活动,能让主体在意象经营过程中自觉关注“物”、“我”交融的创作心理历程,从而使其意象经营显示出多角度性、多层次性,这也奠定了古代诗歌意象的基本范式,促进了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经营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赵险峰[5]2008年在《南宋骚体文学研究》文中认为骚体,是一种独立独特的文体样式。骚体在产生阶段,受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诗体的广泛影响,但整体看来,骚体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楚文化是骚体产生的天然土壤,楚地民歌和祭祀歌谣是骚体形成的直接渊源,骚体是屈原对传统学术文化多元继承并进行创造性加工的结果。骚体独特的文体特征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从形式上来说,骚体以句中是否带有特殊虚词“兮”为判断依据,由“兮”字组构而成的特殊句式是骚体判定上的重要标准;从内容上来讲,骚体文学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并且善于表达哀怨愤懑之情,这些要素构成了骚体的内在情感特质或内在精神。汉代尤其是汉初人们对文体的概念还很模糊,文体分类的意识处于萌发阶段,所以造成了骚赋不分的现象。赋体对骚体有所学习,绝对不能等同于骚赋同源同体。骚体和赋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体样式。南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整个南宋时期,宋王朝与金王朝都处于对峙的局势,连年的战乱,使人民饱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之苦;南宋政府的腐朽统治,苛刻沉重的赋税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些社会现实对南宋骚体文学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南宋对佛、道两教采取保护、鼓励的措施,佛家和道家文化也得以广泛传播。骚体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道、理叁家思想的巨大影响,出现了不少表现佛、道、理思想的作品。南宋骚体文学发展可以分为叁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两宋之际到南宋初年,这一时期骚体创作相对平淡;第二个阶段是孝宗时期到理宗时期,是骚体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第叁个阶段是从宋理宗时期直到南宋灭亡,这一时期是骚体文学发展的落潮期,较之前一阶段骚体创作有所回落。南宋骚体文学分布范围很广,主要分布在骚体诗、以赋名篇的骚体、哀祭类作品及庙记、碑志类铭文中。南宋骚体文学的题材涉及到很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第一类是充满忧患意识的感物咏怀之作。南宋文人将对故土的依恋怀念之情和对国家的忠愤之情,全部都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之中,谱写出了可歌可泣的爱国强音。在关心时局、关注现实的同时,骚体文学中也有一些个人情感的流露,在以咏怀为题材的骚体中,感叹季节变换、人生蹉跎的感时伤时之作与追念古人的咏史怀古之作也有占有很大比例。第二类是贴近日常生活的写景咏物之作。以传统的题材内容为创作对象的篇目,仍然占据了相当大的数量,一些其他的题材也进入到了骚体创作的范围之内,如书斋及日常生活常用之物。南宋的写景咏物类骚体创作,在创作上有两个倾向:一是摹形状物,注重写实性和模仿性;二是物我交融,注重写意和意境的营造。两种倾向相比较,后者的作品分布更多一些,且在艺术成就及思想内容方面较之前者要丰满得多。第叁类是反映理学情趣、道家思想和佛禅之意的骚体作品。南宋理学盛行,道教和佛教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儒”、“释”、“道”思想广泛传播。受这叁家思想的影响,南宋骚体文学中出现了一类表现理学之趣、道家之思和佛家之意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直接与“道”、“佛”两教的活动有关,这些作品或是以说理为主,或是情理结合,是南宋骚体中较有哲学蕴味的一类。第四类是悼亡祭奠、祭祀祈福之作。南宋骚体作品中,以悼念亡灵、祭奠死者和祭祀神灵为题材的作品数量十分庞大。前一种题材主要集中在墓志铭文和祭文之中,在内容方面,或是表达对死者的哀悼惋惜之情,或是记述死者的生平事迹,赞颂其品德操守,多抒发一种哀痛悲伤的感情。而后一种祭祀类作品多是以赞颂神灵和祈求福佑为主要内容的,多表达一种对神灵的敬畏之情和渴望生活安居乐业的愿望。南宋骚体文学在艺术特色方面,既体现出了对前代的继承,也出现了一定的新变。在体式方面,在继承原初骚体体式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异形态。南宋骚体或是以原初骚体的体式来创作,或是同一篇文章中出现多种骚体体式,出现了各种骚体体式相互结合的形态。同时,骚体与其他诗、赋等艺术形式的互相渗透掺杂又造成了骚体与散体相互结合的骚散兼存的体式特征。南宋骚体文学也体现出了散化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是形式上的骚散结合;表现手法上的多样化,出现议论、叙事、说理等多种表达方式;语言上的不事雕琢、追求平易自然,将散文的气势注入骚体创作。南宋骚体文学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对原初骚体中的“香草美人”象征、比兴传统的继承;文人的审美情趣、意象的择取、意境的创造、语言的使用等方面体现出来的由雅转俗的趋向,等等。南宋骚体更加趋于平易化,呈现出疏放晓畅的风格。
戴志钧[6]1997年在《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叁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叁个不同层次,产生叁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叁)《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叁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叁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刘俊菲[7]2013年在《《离骚》中“香草”意象的研究综述》文中认为本文对《离骚》的"香草"意象研究做一学术史整理,古代"譬喻"说的传统源远流长,近现代研究者在研究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当代研究视角更多元,也存在很多不足,如:理论掌握不深入,翻译研究欠缺等,希望这一认识能够对《离骚》中"香草"意象研究问题提供启示和借鉴。
刘佳莹[8]2002年在《何谓“香草美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罗大冈在《告别象牙之塔》中说:“他们发表的作品,都是唯美派的诗歌或抒情散文,不是名山大川,茂林修竹,就是风花雪月,香草美人。”这里,作者误把“香草美人”当作闲适文字、无聊词章理解了。其实,最初是屈原在《离骚》中把楚怀王比作“美人”,把贤臣比作“香草”
陈冬[9]2010年在《论屈大均词对楚骚传统的继承及风格衍变》文中研究指明明末清初,屈大均词继承楚骚传统并由此展开风格的衍变的。他标榜为屈原后裔,因受楚骚传统影响而最终衍变为骚雅品格的词风,体现了传统文人在祖述前人传统方面的努力以及在词风衍变方面的路向,也为由此切入对当时词坛风气内在衍变规律的探讨提供一定参考意义。在引言部分,简单介绍屈大均词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主体部分由叁个方面展开:第一章,以屈大均对理想人格和道德精神的推崇和追求以及对文学观念产生的影响为考察重点。他在“风雅精神”指引下,深受楚骚抒情言志传统影响,在词学观念上易倾向于实用精神。这部分侧重于词人主体精神方面的考察。第二章,以屈大均词中表现的情志与楚骚精神的联系以及体现的楚骚传统为考察的主要内容。涉及“香草美人”、“哀郢招魂”、“自适之适”等方面内容,可见屈大均词与楚骚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和风格衍变的清理依据,这部分侧重于从屈大均词的题材内容方面考察。第叁章,以探讨屈大均词的骚雅词风及其形成过程为主要内容。这固然与他的词对楚骚传统的自觉继承有关,同时清初词本身的运动规律以及当时词坛的风气、政治形势、社会心理的转变,都促成了屈大均词的骚雅词风的形成,这恰与当时词坛盛行的浙西骚雅词风的偶合。总之,屈大均词继承楚骚传统并形成对骚雅词风的追求和模仿,体现了传统文人在认祖归宗的思想情结上,并进而在词学观念上受到的激励和影响,也预流了当时词坛风气衍变的必然路向。
殷晓燕, 万平[10]2016年在《诗歌中的“面具”美学——从屈原“香草美人”之“引类譬喻”模式说起》文中研究表明屈原《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草"和"美人"意象的使用,诗人使用大量笔墨描绘了芬美芳香的植物意象以及极富女性魅力的"美人"形象。"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夙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他将香草佩饰身上,使之与己连为一体,成为其美好人格的象
参考文献:
[1]. 《离骚》“香草美人”抒情模式研究[D]. 刘志宏. 首都师范大学. 2003
[2]. 从符号—结构谈《离骚》和《神曲》的文学手法[D]. 马迎春. 重庆师范大学. 2014
[3]. 汉代楚辞学研究[D]. 纪晓建. 苏州大学. 2014
[4]. 楚辞意象之构成考论[D]. 罗建新. 上海大学. 2010
[5]. 南宋骚体文学研究[D]. 赵险峰. 河北大学. 2008
[6]. 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J]. 戴志钧. 北方论丛. 1997
[7]. 《离骚》中“香草”意象的研究综述[J]. 刘俊菲. 青年文学家. 2013
[8]. 何谓“香草美人”[J]. 刘佳莹. 咬文嚼字. 2002
[9]. 论屈大均词对楚骚传统的继承及风格衍变[D]. 陈冬. 西南大学. 2010
[10]. 诗歌中的“面具”美学——从屈原“香草美人”之“引类譬喻”模式说起[J]. 殷晓燕, 万平. 文艺评论. 2016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楚辞论文; 屈原论文; 离骚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神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