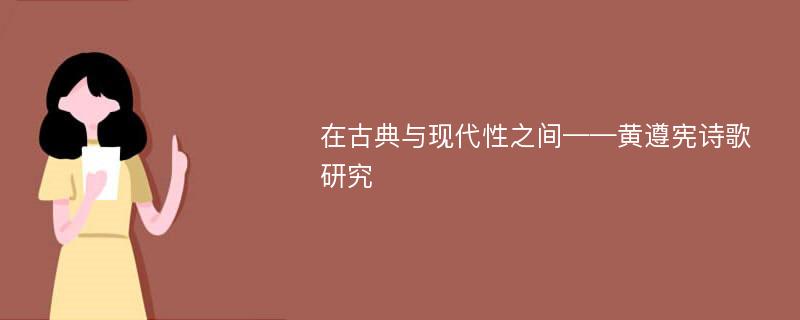
刘冰冰[1]2003年在《在古典与现代性之间》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现代性问题逐渐成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等领域共同关注的学术热点之一。现代性理论也为近代诗歌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视野。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在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型中无疑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外交官,他有幸较早地体验到了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又以此来反观中国,并以这一独特视角,以诗歌的形式描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形象。因此,他的诗歌有着特殊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对于他的诗歌创作的研究,目前还基本上处于传统的赏析阶段,鲜有从心理体验、审美特征、艺术情趣等层面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论述。本文拟借用现代性理论对黄遵宪诗歌进行一番总体关照,并不揣浅陋地希望以此来深化现代性理论的研究。 本文的主体部分由叁章组成,主要从黄遵宪的诗歌理论、诗歌创作、艺术风格(“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等几个方面对黄遵宪的诗学观念及其诗歌文本进行分析论述。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宋成为永远不可企及的规范,但同时也意味着这种规范造出了自身的美学危机。所有后来者的想象力都在这种辉煌面前失去了自信,除了在前人智慧的缝隙里讨生活,几乎没有新路可走。十九世纪中叶,来自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强烈震撼,迫使中国人从政治、经济、军事、直到文学艺术等各个层面来反省自己的生存危机。一批志在改造社会的先觉者在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下,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诗歌这一原本在文人士大夫手中吟咏把玩的精致形式成了启蒙者新民的工具。于是,诗歌的教化功能和艺术形式之间的矛盾及其能否与时代相适应的问题就摆在了近代诗人的面前。 面对古典诗歌自身的种种困境,近代以来,各个诗派都在寻找出路,试图有所突破。黄遵宪也提出了他的诗学观念。他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主张作诗以“言志”,但其具体的表现内容已与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要求大不相同。他所关注的是对拯救时弊、社会改革有用的价值理念。在他的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国家观念、民族平等、科学理念、异域风情以及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的辐射所感受到的痛苦与惊羡的体验,都是古典诗歌审美范围内不曾出现的。他反对诗坛上那
胡峰[2]2010年在《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文中指出晚清文学的研究越来越热,其中的诗界革命研究同样如此。但从诗歌本体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诗歌内部世界的新变与转型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力图进入诗歌的本体世界,对诗歌的语言、声韵节奏、意象及文体诸要素进行具体考察,从中探寻现代新诗发生的历史根据与内在动力,凸显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发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所用的“本体”概念,主要是指构成诗歌审美世界的诸多要素的形态及特征,主要包括语言、声律节奏、意象、文体等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是诗之所以成为诗的必备条件,而且也决定着诗歌的审美面貌与呈现风格。考察诗歌的转型轨迹,这些要素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必须作为研究的重心。为避免形式主义研究存在的片面性,本论文拟运用发生学原理、文化研究、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理论,采用文化学、历史与审美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诗界革命的诗歌本体进行整体观照与文本细读。从诗歌本体的角度看,研究者对诗界革命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仍存在一定的误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早期的“新学诗”置于诗界革命的范畴之外而不顾。本文重新发掘了“新学诗”的文学意义及历史价值,并把它还原为诗界革命的开端。同时还纠正了诗界革命并非诗歌“革命”而是“改良”的认识,进而对诗界革命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整体梳理。第一章主要从诗歌的基础——语言切入,指出诗界革命已经催生了早期的白话诗。该章首先分析了诗界革命中语言变化的背景与动力,指出诗界革命的语言变革是处于晚清语言文字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而展开的。梁启超、黄遵宪等诗界革命的先驱与现代新诗的早期诗人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语言是他们寻求诗歌变革的共同突破口,进化论的思想是其共同的理论武器,而采纳口语、方言、外来语入诗则是他们共同的变革策略与追求目标。这其实就标志着现代白话语言的最初的诞生。黄遵宪率先提出“我手写我口”的倡议,确立了以口语对抗文言的方策。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宣传者对口语的推广使用使口语得以普及。诗界革命的诗人主要是看中了口语自身的鲜活性、通俗性、晓畅性、交际的便捷性以及明显的主体性等特征。而这正好契合并启发了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出台。方言除了具有口语的一般特征,还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最突出的就是它以边缘化的身份形成对主流文言的对抗姿态,反叛性与抗争性自然蕴含其中。除此之外,方言还以不同的地域特色来丰富诗歌的语言与审美世界。方言入诗不仅体现在早期白话诗人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人的创作中,而且也受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的青睐。而方言自身的矛盾与张力,正是其具有长久生命的关键所在。从最初的“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新学诗”开始,诗界革命的同人们就开始把新名词引入诗歌创作这一“高尚的楼台”里,后来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目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新名词仍可以留存在诗歌中。新名词的介入不仅标识着一种新思想的出现,而且还会引起诗歌本体的变化,比如声韵节奏的调整与语法句法的变化等,并进而改变诗歌传情达意的方式与效果。现代新诗中的新名词与新语句更为突出,在郭沫若等诗人那里甚至出现了直接移植外来词汇入诗的现象,外来词汇所代表的新事物被改造成诗歌意象的情形也不乏其例。口语、方言、新名词新语句等不同风格、不同形态的语言既动摇了传统诗歌的语言基础,同时也为新型诗歌的孕育与诞生耕耘了土壤,预示了方向。第二章重点分析诗界革命中的诗歌创作在声韵节奏上对传统诗歌的突围与创新,这是诗歌从传统的格律模式向现代自由声韵节奏转型的重要表现。声音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个侧面,而诗歌对声音的依赖性又远远超过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类型。诗歌古体近体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声韵节奏作为衡量标尺的,而诗歌本体的变化也势必体现在声律节奏方面。诗界革命对传统诗歌的反叛也体现在对其固定严密的声韵节奏的颠覆上。首先在声韵规则上,近体诗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使稍有违反即“拗”也要及时予以补救。诗界革命的创作则频频触犯近体诗的大忌——出韵,把近体诗中严禁使用的不同声韵有意排列在同一首诗中;同时通过使用近体诗中罕见的仄韵,突破了近体诗与古体诗的界限;而对平仄规则的违背,更是彻底解构了近体诗的声律规范。有的诗作甚至舍弃了古体诗相对自由宽松的声律限制,而采纳了超越于近体诗与古体诗之外的全新的诗体形式。这不仅是诗人自觉反叛自唐代以来的声韵传统的具体体现,更是一种新的诗歌声韵形式的预示与开端。它昭示着将来的诗歌会在既已成型的声律规范之外寻求更为自由、广阔的声韵形式,从而朝着自由诗体的方向拓展开来。在胡适的早期诗歌中,重古风轻格律的现象也极为突出;稍后出现的自由体诗歌,则彻底抛弃了近体诗与古体诗的声律模式,把诗界革命中对声律节奏的突破精神发扬光大。其次,诗界革命还对传统诗歌的节奏模式进行了大胆的“破解”。在词语的组成上,诗人采用了双音节、叁音节乃至更多音节的词汇入诗,使得传统诗歌的节奏划分模式难以为继;在音节的排列组合规律上,也突破了传统节奏的程式化规则,即五言的“二二一”(或“二叁”)、七言的“二二二一”(或“二二叁”)规律,在七言诗中甚至出现了“六一”的节奏形式,显然违背了先抑后扬的传统诗歌的语言规则;而语义组与语音组不能两全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另外,散文中常用的“之”、“乎”、“者”等语助辞也频频冲击着诗歌的传统节奏模式。声韵节奏上的这些变化更能够契合并张扬创作主体的现代情感与体验。这种调整与更新的意义是双重的:既在继承与改造传统的同时开启了现代格律诗发展的通道,又在此基础上催生并启发了现代自由体诗的诞生。而现代自由体诗和现代格律诗的同时并存与此消彼涨,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历程。第叁章着眼于对诗界革命中意象使用情况的分析,指出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意象已经显露出现代性的特质与趋向。诗歌中的意象是指寄寓了诗人情感与意念的客观事物,它与诗歌特别是中国诗人以形象思维见长的特点密切相关。诗界革命对诗歌本体的改造,同样也以意象作为对象与表现形式。首先,在物象的选择和改造上,诗界革命增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事物作为意象的基础构成,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物象的范围与表现能力;与此同时,在原有事物或景物的基础上,通过寄寓传达诗人新的情感体验与思想认知,同样使原有的“象”与新颖的“意”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意象类型。其次,诗界革命的创作还把传统诗歌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事象叙写作为表现的重点表现出来。事象的增加既是诗人理性分析与归纳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又使得诗歌增强了叙事情节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同时促进了表述方式的精确与具体化,另外对诗歌声律也具有一定的改造功能。因此,诗界革命中偏重于事象叙写的诗歌繁盛的现实,正是诗歌本体结构与外在形态由传统格律诗向现代自由诗过渡的重要表征之一。除此之外,诗界革命的创作者把大量的抽象的概念名词引领进诗歌的殿堂,这自然会挤压意象占有的空间并影响其在诗歌中的地位。而这种抽象名词的出现,不仅影响了诗歌的声韵节奏、对仗、诗体形式,而且还迫使诗歌的表意手段及功能由具象向抽象转变,从而催生了现代说理诗的发生。第四章重点考察诗歌文体结构与形式向现代诗体形式的转型。诗界革命的创作成果在诗体形式上开始呈现出现代自由体诗歌的特征。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是作家、批评家独特的感觉方式、体验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结构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上述各种因素的直接体现。诗界革命中的诗歌文体受外部环境、作家观念、传播工具特别是语言等诗歌本体要素的共同作用,无法固守原来的结构特征与文体形式,“变”成为其继续生存的不二选择。在“变”的具体路向上,诗人们首先选择了具有新鲜活泼的文体特性的民谣作为资源与镜鉴,以此来消解“庙堂”诗歌的僵化雕琢与固步自封;同时,不同地域的民谣含蕴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它的出现同样能够起到丰富诗歌文体类型的作用。其次,为了恢复诗歌的音乐本性,诗人们还大力倡导并积极实践歌体诗创作。他们分别以歌行体为模板,同时汲取异域音乐资源进行歌体诗的独创与普及,试图以音乐特有的感染力、形式上的自由灵活而又不失诗歌旋律的特征改造旧体形式,实现诗歌体式的创新。再次,采纳“以文为诗”的创造策略进一步解放诗体,以不拘形式、不拘格律的散文化特征把诗歌文体引领进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天地。这种散文化的诗体形式主要表现为以虚字、口语词汇以及新名词入诗,在对仗、韵律、节奏上逐渐脱离传统格律诗的模式,诗行上则呈现出长短不一、灵活多变的散文化句式。这不仅更新了传统诗歌单一稳定的文体形式,而且也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与表达效果。同时,更是诗人主体意识与精神结构的集中体现。这种诗体上的创新策略与发展路向,不仅为现代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样板参照,而且也成为新诗体式建构的一致路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诗界革命之于现代新诗发生的意义进行论析。主要分析了诗歌创作作为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外在环境(世界)、创作主体(诗人)、接受者(读者)以及诗歌文本(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特别是它们对现代新诗的发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外界环境还是创作主体,抑或是接受主体,他们的变化必定会影响诗歌本体并通过它表现出来。而且,诗歌的转型研究也必须以诗歌本体的变化为中心,因此诗界革命在语言、声韵节奏、意象以及文体结构及形态的变化对于现代新诗的发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诗歌本体的嬗变成为现代新诗发生、发展的最突出表征与路向标。而诗界革命是现代新诗发生的雏形与预演。
隋明辉[3]2016年在《黄遵宪诗歌的语言特征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地位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自西周、秦、汉魏发展到唐宋,中国的古典诗歌到达全盛。唐宋以后,诗歌自金式微,元代散曲、明代传奇各领时代风骚,而在清代晚期之前,虽然诗歌流派众多,但难免拘泥于前人,没有跳脱前人诗作的禁锢。十九世纪中下叶,国门大开,近代西方文明对当时闭关自守的社会带来了猛烈冲击,迫使一群有志于变革的先觉者,尝试着去寻求救世救民的良方,同时也为中国的古典诗歌带来了新变。黄遵宪就是其中之一。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不仅亲身见证了置身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下的晚清社会的摇摇欲坠,也因其外交官的身份,走遍五洲四海,体验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而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他的诗歌创作有着古典性与现实性相碰撞的显着痕迹,因此也具有特殊价值。目前对黄遵宪诗歌的学术研究为数不少,但是大部分研究集中在黄遵宪生平、其诗歌创作的发展阶段、黄诗的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领域,而恰恰在“诗歌是艺术化了的语言”这一本质特性上有所欠缺。所以本文的立意是:结合先前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具体的语言学分析对黄诗这一文学现象展开研究,目的是通过较详细严谨的语言学分析展现黄遵宪诗歌的特点和发展历程,并以此为突破点,结合前人对黄遵宪及其诗作的评议,探究其在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四章构成:第一章介绍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第二章简述黄遵宪的生平,分为青少年时期、驻外时期、归国力推新政时期叁个阶段;第叁章通过修辞、词汇、音节、句类等语言学角度对一定量黄诗进行分析,展现其诗歌创作的特点和流变:第四章讨论黄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的形成。
赖彧煌[4]2008年在《论古典成规牵引下的晚清诗歌革新》文中指出文章探讨了晚清诗歌革新的"难度",新名词、新事物的书写只是诗歌意象系统的调整,晚清诗歌革新包括颇有新形式试验特征的"杂歌谣"的搁浅是因为强大的古典成规的牵引,古典成规是诗歌书写中的深度"装置".
李玲[5]2013年在《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文中认为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过程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阶段。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以文学救国,发起“诗界革命”。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前后两年间,梁启超对黄遵宪“从略有微词到全力歌颂”。在《饮冰室诗话》中大力推崇他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长篇诗作,表彰黄诗“存吾国,主吾种,续吾教”。受梁启超的影响,黄遵宪在古典诗坛中备受关注,时人撰着诗话,争收人境庐诗。从政治文化的中心上海、北京,到政治文化的边角香港;从主流报刊到非主流报刊;从维新派到一般诗人、学者;都对黄遵宪的诗作和政治事功予以佳评,黄遵宪誉满天下。虽然各家诗话都没有象《饮冰室诗话》那样视黄遵宪为第一流的诗人,但都赞赏他的域外诗和抚时感事诗,公认人境庐诗的开新价值和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可贵精神。在文学革命之前,黄遵宪不是单一的“诗界革命”偶像符号,他文学上承载的形象和意义是多元复杂的。这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他是在古典诗歌的谱系下被推崇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开文学史着作论述黄遵宪诗歌的先河,围绕着“我手写我口”来表彰黄遵宪倡导白话文的贡献。胡适回溯诗界革命找寻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根源,而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又有白话诗作,于是被提拔为白话文的先行者。由此黄遵宪新旧两属,既是晚清诗歌改良运动的代表诗人,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开始了黄遵宪在新文学的视野下被推尊的过程。胡适的影响下,1920—1940年北京上海广东争相梓印人境庐诗、笺注人境庐诗、刊布人境庐遗作,于是读者翘首以盼的黄遵宪诗集和遗稿近乎井喷出现。既有黄遵宪乡人为了建构客家中原根源认同而选笺人境庐诗,亦有胡适信徒青年大学生校点人境庐诗,亦有守护文言诗传统的青年诗评家全注诗集,也有黄氏后人争先恐后地重印诗集,密集刊布遗稿。随着诗集出版热潮和遗稿的密集刊布而来的,是人境庐诗的研究热潮,时人的文学史着、诗话络绎缤纷叙论黄诗。1920—1949年的断代文学史、文学通史和文学专题史(总共26种)纷纷叙及黄遵宪。除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少数几种文学史着外,大多数文学史着(其中大多是师范、高中教材)叙论黄遵宪的角度比较单一,内容大同小异,郑振铎、陈子展等人编撰文学史采用了梁胡二大师对黄遵宪的评述,而后的文学史着又取资郑振铎、陈子展等人撰着的文学史,如此陈陈相因,摭拾梁启超、胡适的观点而成定论。黄遵宪被众多文学史着纳入为重点作家,标志着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奠定了。这些文学史着经由教学,向一代学子提供了黄遵宪是一个伟大诗人、爱国诗人、白话文先驱的共同论述。这种共同论述,具有传承性,影响着一代学子的行为和思考模式,这代学子传灯接力,一脉相承,为黄遵宪持续稳定地在1949年之后保留文学史的一席地位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基本上奠基于20世纪之前的叁、四十年,也即是皆奠基于“近代”以及“五四”学术群体。之后黄遵宪研究,不同程度不因袭、重复、引申胡适的观点,使黄遵宪坐稳了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地位。与文学史着叙论黄遵宪的内容单调而重复相比,文学革命之后的七家诗话选评黄诗,虽片段只言,但是内容丰富多面,既有沿袭前朝梁启超、狄葆贤、潘飞声、陈衍等各家诗话的观点而推崇其域外诗和感事爱国诗,也有针对黄诗研究的热点问题的争议,也有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赞赏黄诗,还有结合时代的反帝爱国的主潮来品读黄诗的诗史特色,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见解,由此“可知公度诗近年来已被人们热烈地研究之一斑了。”与文学史撰着者大多为五四学术社群的成员不同,诗话的撰着者虽然不是旧朝遗老遗少,他们政治观念上大都趋新,但是他们酷爱传统文学,反对尽弃文言,爱惜旧体诗,有心赓续诗学传统,有意识地运用诗话这种古老的文体来包容时代思想。从他们的诗话论评黄诗来看,与文学史着叙论黄诗摭拾他人陈言为定论相比,他们独到的见解多,内容多面丰富,精彩纷呈,显见了黄诗在民国古典诗学中仍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就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和奠定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由新文学导师胡适接力推崇黄遵宪,推助了黄诗热。1920、1930年代黄诗研究热潮,固然是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汇集而导致的,反映出黄遵宪得到新派旧派两方的赞颂,但是政治情势,“国难日深,国亡有日”的关头,《人境庐诗草》中大量的感事诗作有救亡之助,也有力地推助了黄诗的刊布和研究热潮。
赖彧煌[6]2008年在《论晚清步调不一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评价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可以联系他们对小说界革命的看法,他们面对两种文类革新时发言的姿态是很不一样的。在以激进的言论探讨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对诗界革命的态度却是审慎的,甚至趋向保守的。这说明不同的文类成规对美学变革有不同的制约作用。梳理和比较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面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不同反应,可以借此更深入地反思古典成规对诗歌革新的强大牵引力。
孟旭琼[7]2008年在《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文献学价值研究》文中认为《日本国志》是黄遵宪任驻日使馆参赞时所写的一部围绕日本明治维新史而迫切要求对我国的各项体制进行改革的一部巨着,被誉为19世纪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作。本文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黄遵宪《日本国志》的价值进行审视,以期略补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全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面对《日本国志》的写作缘起做了分析,并对其编纂过程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着重对《日本国志》诸种版本的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以窥见《日本国志》的学术源流。第叁部分着重从对中日史料的征引、交往与笔谈、实地考察等方面对《日本国志》的资料来源进行了阐述。指出,《日本国志》所引用的中日文献资料皆为权威性着述;与黄遵宪交往和笔谈的日本友人均是当时日本国内有名的汉学家,对日本史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为《日本国志》的编纂提供了诸多帮助;作者通过实地考察,也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保证了《日本国志》的学术性。第四部分着重对《日本国志》所包含的文献编纂思想和编纂特点做了条分缕析。指出,《日本国志》中所体现的务从实录、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文献编纂思想;在对资料进行采集时谨遵博、精、善的原则;志体、史表、史评叁位一体的文献编纂形式,叁者实是对我国传统文献编纂思想与方法的继承和创新。第五部分主要是对《日本国志》的史料价值做了系统地阐述,以彰显其于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及文献学史上的地位。总之,黄遵宪《日本国志》所蕴含的文献编纂思想,志体、史表、史评叁位一体的文献编纂形式,以独特的视角所记述的丰富而真实的内容,以及较高的史料价值乃至社会功用,使其不仅在当时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在今天仍有其非常高的文献学价值,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党月异[8]2014年在《王韬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文学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王韬的影响不容忽视。王韬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融贯中西的文化背景使其文学作品在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小说、诗歌、散文,包括从文学观念、内容题材、传播方式、文学语言到文学功能,都开启或推动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历程。
参考文献:
[1]. 在古典与现代性之间[D]. 刘冰冰. 山东大学. 2003
[2]. 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D]. 胡峰.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3]. 黄遵宪诗歌的语言特征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地位的形成[D]. 隋明辉. 山东大学. 2016
[4]. 论古典成规牵引下的晚清诗歌革新[J]. 赖彧煌.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5]. 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D]. 李玲. 苏州大学. 2013
[6]. 论晚清步调不一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中心[J]. 赖彧煌. 莆田学院学报. 2008
[7].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文献学价值研究[D]. 孟旭琼.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8]. 王韬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J]. 党月异. 新疆社会科学. 2014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黄遵宪论文; 诗歌论文; 梁启超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古典语言论文; 读书论文; 现代性论文; 革命论文; 晚清论文; 日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