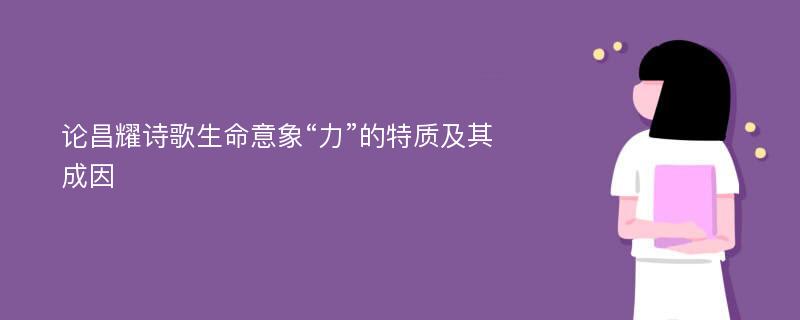
王昌忠[1]2003年在《论昌耀诗歌生命意象“力”的特质及其成因》文中认为生命意识是诗人昌耀始终如一的诗歌意识。本文以“生命”作为解读昌耀诗歌的切入点,并将其长达数十年、且具有明显时段性特征的诗歌统摄于“生命”这一精神总主题之下。昌耀的诗歌意象即生命意象,而昌耀形态各异的生命意象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质态相同的生命意象。这种“内在一致性”即拼搏的、进击的、抗争的、创造的特性,也就是力的体现和张扬的特性。 昌耀营构生命意象的目的,就在于传达生命这种相同的质态。本文顺应着昌耀的生命经历和精神延伸秩序,分四个时段观照、把握了昌耀的生命意象特征及其张扬生命力的方式:一、山旅:生命强力的感性观照。在此阶段,昌耀的精神路向也出现了转折和递进。昌耀通过“山旅”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呈示出直接、具体、真实和外化、感性、显在的特质。二、慈航:生命创造力的特别体认。此时段,昌耀对自身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群体生命的打量和品评,冷静、沉实也深入、提升了。生而后死、死而后生的生死体验,“激励”他主要关注生命的“生”——新生和再生;而通过这“生”,昌耀张扬的是生命的创造力、生殖力和繁衍力;“开发”和“挖掘”的,是这创造力、生殖力和繁衍力的来源和起因:情,爱,善,美和良知!叁、圣迹:“大生命力”的强劲传达。在精神心灵最强劲、最旺盛的此时段,他用恢宏而辉煌的诗歌系列:《旷原之野》、《青藏高原的形体》、《巨灵》、《牛王》等等,完成了西部大高原的造型。昌耀堆垒的是“大生命”意象,张扬的是扩大了“量”、提高了“质”的“大生命”的“大生命力”。四、赶路:生命内力的深度领悟。此时段,伴随诗歌悲剧意识的膨胀、扩大和深入、内化,此时段,昌耀展现和张扬的是生命的强大内力,是拷问生命终极意义的、内在生命和灵魂的毅力和意志力。 昌耀诗歌的生命意象,是诗人把在漫长而艰辛的生命历程中所领悟、体认的生命立场、生命理念,贯注、交汇进他捕捉、选取到的事象、物象而形成了的。这些生命意象本身就是诗人自身生命的显影和聚形、比拟和参照。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力求将“诗”和“人”结合起来,通过“解读”昌耀生命解读其诗歌中的生命意象。
丁凯[2]2010年在《昌耀研究述评》文中认为昌耀及其诗歌的价值是一个逐渐被认识的过程,今天,其作为新诗史上大诗人的地位已被肯定,但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对于昌耀诗歌及其生平资料的分析研究还远未达到充分的空间。
丁凯[3]2011年在《滚石者的孤独与崇高》文中研究表明在昌耀的诗歌写作中,英雄特性、对苦难的体认和超越、对生之认同及对意义的求索与求索中的困惑等因素及因素的交织,构成其诗歌世界的悲壮性气质。在其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的不同阶段,这种悲壮性气质以或显或隐、或浓烈或沉郁的方式呈现。早期,被难荒原、身处忧患,在同期及回归初期(80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中,昌耀以爱和信念为支撑,对生命、生活、不幸、家园书以阳刚、悲悯与多彩主题,以期在精神救赎中实现对苦难的超越、对宿命的嘲弄,是悲壮在显性写作中的隐性呈现。80年代中期及以后,面对社会、思想、生存、写作、生活和情感上的矛盾,昌耀有所困惑,身处孤独但仍然追寻并追问,没有回答,但仍然坚持,于是,在两极的张力与空寂中悲壮性进一步加深、扩大,这一切都体现在诗歌中。笔者试图在笔力所及的范围内对这一悲壮性进程进行分析。论文在绪论第一部分对昌耀生平及其诗歌作一次轮廓性描述,第二部分对‘滚石者”进行界说同时表明本文写作缘起。第一章主要以昌耀早期及回归初期的诗歌作品为例证,论述昌耀以爱和信念实现对生活苦难与命运不幸的超越,是悲壮的阳刚性体现。第二章,引用的诗歌以昌耀回归中期的作品为中轴向两方递进,来分析其诗作中的几组主导性意象群,试图使其诗歌的悲壮性特征进一步凸显,本章同时具有承接的作用。第叁章,分析在内外力的挤压和撕扯下昌耀的诗歌写作,这是一个进取与踟蹰、追寻而焦灼、发问而无所得的阶段,也是悲壮性的最大化。悲剧强调的是其结局,而悲壮则是悲剧中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过程,是悲剧的升华。虽然昌耀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余生,但笔者仍视其为对命运的最后一搏,用诗性的姿态向世界说再见,是——悲壮的。
陈天[4]2016年在《新世纪以来的昌耀诗歌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的昌耀研究呈现出全面纵深的态势,论文拟从昌耀诗歌的主题嬗变与学界对其创作阶段的划分、昌耀各阶段诗歌的总体研究以及昌耀诗歌的审美意蕴与诗学特质等方面展开综述,以期能在集成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彰显昌耀诗歌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王晶[5]2011年在《论昌耀反抗人格在诗歌中的表现》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昌耀诗歌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这种反抗人格赋予其诗歌的反抗性,并且说明其诗歌创作是他对苦难和命运的残暴反抗一生的结果。文章以昌耀一生中的叁次苦难为经线,以诗人罹难“传统悲剧”到“人本悲剧”的变化为纬线,从一生诗歌写作的维度展现这叁次悲剧所带来的诗歌面貌及反抗本质:全文分为叁章:第一章,证明诗人早期诗歌中对于英雄与土地的渴慕以及八十年代前期对于高原的回望中体味到爱与良知的力量,是高原作为诗人精神家园的馈赠,也正是因此诗人才有信仰反抗时代的灾难。第二章,证明诗人中后期诗歌中表现出对于政治乌托邦精神的持续高扬和呼唤、对于苦行僧式修行的痴迷和对于爱情热烈的——拥抱,都是他在城市生活逐渐展示出庸锁和艰难时,妄图寻找到新的支点的努力。第叁章,证明诗人在晚期诗歌中越来越多对于焦虑和荒诞的书写,实际上是他内心对于诗歌意义逐渐偏离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意识到时间的飞逝和生命的有限后的呈现,而远游和对于宿命论的笃信也成为诗人最后的武器,然而带来的结果却是更深的失望。最后一部分为结论。诗人的一生诗歌创作是诗人反抗人格对外界及内心的反抗的艺术化表现。同时,诗人的反抗人格也让诗歌作品富有了更为深厚及崇高的悲壮美。
参考文献:
[1]. 论昌耀诗歌生命意象“力”的特质及其成因[D]. 王昌忠. 浙江师范大学. 2003
[2]. 昌耀研究述评[J]. 丁凯.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0
[3]. 滚石者的孤独与崇高[D]. 丁凯. 西南大学. 2011
[4]. 新世纪以来的昌耀诗歌研究综述[J]. 陈天.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2016
[5]. 论昌耀反抗人格在诗歌中的表现[D]. 王晶. 浙江大学.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