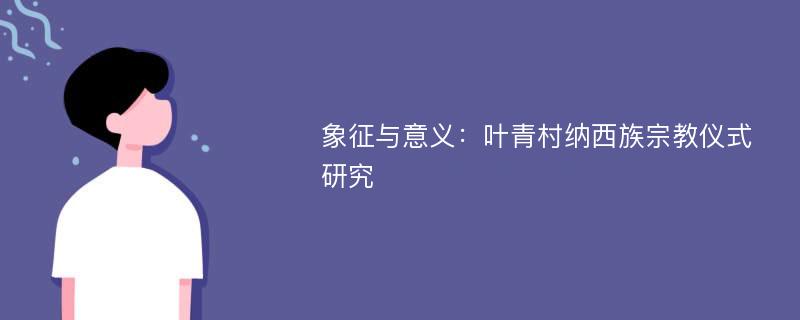
鲍江[1]2003年在《象征与意义:叶青村纳西族宗教仪式研究》文中提出在宗教情景中,跪拜意味着什么?脱帽意味着什么?献花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表达生发意义,其基础又在哪里?这些貌似简单却又难于讲清楚的问题就是本项目的研究主题。 本项研究以感觉和认知为切入点,通过象征符号与意义分析,揭示作为叶青东巴教仪式表达生发意义基础的宇宙论人观建构,并由之出发对东巴教仪式的实质内涵——人通过祭司东巴与叁界超越存在进行文化交流及其过程性的叁阶规律作出阐发。 东巴教宇宙论中,“萨”和“俄亨”是两个最根柢的理念。具再生产性的世间万物除可感知的具体形态外,均内在有超越具体形态的“萨”存在。起源传说中无形无象的“萨”是世界的起始存在之一,生命的活力依托于“萨”。“俄亨”意为魂灵,属具时空超越性的存在,“俄亨”与身体“古拇”结合构成生命“祀”。“祀”作为生命的意义涵盖面不止于人,但“俄亨”仅与人相关。魂灵与身体结合,依托自然共谋此岸文化生计,魂灵消费产品内在的“萨”,身体消费产品非“萨”的部分。魂灵内在于身体,以身体天灵盖部位为出入之门。共同的生计使魂体结合,但魂灵的超越本性决定其经常性地逸出身体、家屋,到外间游荡。死亡意味着魂体结合“祀”生命的终结,宣告魂与体的彻底分诀。经葬礼,魂灵将携自己以及人间供养品的“萨”,攀升归入上方祖宗居地,角色由“祀俄亨”转变为“日俄亨”(祖魂灵),亦即“日”(祖),依托再生产资源的“萨”从事再生产;而躯体则经火葬回归于尘土。得不到葬礼的亡灵则被滞于中央此岸和下方鬼域,因无“萨”而永远饥饿,惟以作祟于人的方式来获取供养,和缓饥饿。 东巴教信仰建构中,祖宗、神、鬼等不过是超越的魂灵“俄亨”因空间归属差异而生出的不同身份,其中祖宗与神更是同在上方界,无本质差别,祖宗也就是神,只有些神并不是祖宗。神祖与鬼的区别,前者属上方界,后者属下方界。神祖护佑人,得人间文化产品的“萨”供养;相反,鬼魅作祟人,得人间去了“萨”的文化产品补偿。 东巴教的静态大宇宙空间分作上中下叁界,上界神祖境,下界鬼域,中央为自然界主宰“史”的辖境,一切野生动物为其家畜,山川森林土地归其所有。人作为过客在中央界经营文化生计,以魂归上方祖宗境为终极关怀。文化区别于自然,但必须依托于自然,开荒伐木、劈地建房、引水筑路等人类活动都势必侵犯到“史”,所以“史”是窃取人魂作祟于人的一个主角。此岸人生的无奈,除对付鬼魅外,还得时时予“史”以文化产品补偿,免遭失魂之灾。东巴教宇宙论,叁界间没有轮回,人的归宿或者上攀回到祖宗居地,或者不幸滞于中下界,成游魂饿鬼。是归是留系于是否有后人为你请东巴主持法事,这是回归的唯一途径,并且不论正常死亡还是凶死,都有相应的法事途径可觅。 静态的宇宙分作上中下叁界,但是作为具相对意义的认知框架,上与下、里与外是叶青东巴教文化两组最基本的二元对立认知工具,渗入人文社会生活诸领域。这两套认知模型均以魂灵为建构基点,但它们对宇宙的铸模走的是两条相反相承的路径,前者由大及小,由宏观而微观,走空间压缩型认知路径;后者恰恰相反,由小及大,由微观而宏观,走空间膨胀型认知路径。无论如何,上与下,里与外的模型渗入所有纳西人对象化的认知领域,经此而绘出的是整个的宇宙图景。 作为存在本身,宇宙是唯一的宇宙,我是唯一的我,而认知框架是多重的,且在同一框架下也存在多重认知平台,孰轻孰重取决于具体时空场景。譬如,在叶青纳西人上与下这一认知模式下,依托本士知识、年龄、性别、财富、亲属势力、基于广阔政治体系下的权力代理地位、外域知识等维度,构建出错综复杂的社会角色结构体系。现实社会实践中,诸多维度的上与下对立,常常处于矛盾而模糊的状态,个体的选择须根据情景作出主观判断。 纳西族东巴教、具超越性的“俄亨”(魂灵)和“萨”(万物内在能量)是其信仰基石,从宏观到微观走空间压缩路径的上与下对应,以及从微观到宏观走空间膨胀路径的里与外对立,是其最基本的对象化世界的认知模式,人通过媒介人物东巴,与上中下叁界超越存在进行的叁阶式交流是宗教实践的实质内涵。 跪拜、脱帽和献花都表示景仰,但它们各自生发意义的根抵并不相同:跪拜基于上与下二元对立认知模式;脱帽的意义来自魂灵内在于身体,以身体天灵盖部位为出入之门的人观理念;献花的实质是献花儿绽放出的花之“萨”,虽然仪式中己出现单纯表达性的象征替代品一一竹纸花圈和冷杉枝。
和少英[2]2009年在《《象征的来历: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仪式与象征符号理论的研究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犹如"皇冠上的明珠",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迄今为止的众多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流派,都将它作为观察与剖析人类情绪、情感和经验意义的利器,并表现出了对仪式的独特理解与阐释,从而不断推进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无情的现实:国内民族学/人类学学界在仪式与象征符号理论方面的研究却远
冯莉[3]2012年在《民间文化遗产传承的原生性与新生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对于本质主义静态研究模式的质疑和批评,使文化实践、现象、创造和再生产成为当下的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这一背景下,有关“民间文化遗产”的讨论,不应仅仅满足于从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和保护技术的角度来展开,而更应该关注受到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日益强烈影响的民间文化正在经历的变化。本文针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矛盾,就民间文化遗产当代传承问题提出“原生性”与“新生性”概念,以回应国内外理论与之相关的二元对立式争论,并为国家文化保护制度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论文选取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叁坝乡纳西汝卡人村落信仰生活为田野个案,探讨民间文化在当下语境中发生的变迁:村落中正在发生的“传统的发明”以何种途径和手段来完成与原生性文化传统的对接和传续。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同一社群多点调查的方法,结合地方性知识来阐释当下民间文化传承的流动性和互动性模式,并围绕村落历史和现实两种语境讨论文化传承行为的变迁。在民族志书写中,运用多声部叙述方式进行口述史呈现,以表达文化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及其在多元力量交错中对民间文化原生性与新生性因素的应用。全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论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辨析“民间文化”、“民间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并论述“原生性”与“新生性”的观点,梳理本课题相关研究,说明本文研究视角和方法。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阐述纳西汝卡人的生产情况及背景,纳西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与重构。第二章围绕纳西人原生性世界观及主体所承继的信仰体系和文化逻辑,探讨当下村落传承新生性的特质和原因。第叁章从日历(时间)、节日(文化空间)、占卜(行为实践)叁方面,探讨民众在信仰生活中传承的能动性。第四章讨论“东巴”作为“仪式专家”的成长、传承。第五章通过祭天、祭教祖舞仪等分析仪式重构模式、其变迁及其组织的原生性与新生性。通过论述,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为多种力量本着不同目的来实践各自不同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焦点。传承不仅是学者们构建的本真性神话理想,更是民众精神家园和内价值的需求,也是国家政治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诉求。但究其本质而言,民间文化遗产传承恰恰是原生性与新生性的交织和纠缠。而从传承实践来看,无论是相对自足的传承,还是基于保护政策的传承,传承主体在场实践参与的多少,决定着传承中原生性和新生性二者比例的大小,这是构成民间文化当下多样面貌的重要因素。
李技文[4]2011年在《祖先之荫庇》文中认为仪式具有象征性,对仪式象征意义的阐释是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民族学、人类学对仪式象征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在西方一大批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仪式象征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主导象征、仪式过程、象征结构、象征符号、文化阐释等重要的学术理论。亻革家人是我国尚待识别的少数民族群体,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重安江两岸。“哈戎”仪式系亻革家人大型的祭祖仪式,2005年被列入贵州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集中展现亻革家历史、文化和生活的重要载体。目前,学术界对亻革家人的研究多限于族源、历史、语言、文化、工艺美术等方面的概括性描述,这些研究成果不能全面反映出亻革家文化的深层含义。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选取亻革家人“哈戎”仪式为研究个案,从象征人类学的视域,运用仪式象征理论解读其“哈戎”仪式背后的深层意义,藉此反思仪式的象征理论。全文除了导言和结语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民族志的角度对亻革家“哈戎”仪式的操演过程进行了描述;第二章以“祖鼓”这一特殊符号为重点,运用主导象征理论,阐释了“祖鼓”是亻革家人“哈戎”仪式中的主导象征。在这种主导象征架构下,“祖鼓”既是亻革家人的“祖先”的概括性象征,也是表达其“平安吉祥与生命之本、祖先记忆与家族认同”的阐发性象征;第叁章运用仪式过程理论分析了“哈戎”仪式在阈限阶段的象征意义。“哈戎”仪式的过程就是“通过阈限”,在阈限期交融状态下,亻革家人表达了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这些意义是以反结构的特征所呈现出来的。然而,在“哈戎”仪式的阈限期,亻革家人也具有“结构”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结构”——“反结构”套“结构”的一种新的“结构模式”,我将之称为“原结构”。在“原结构”模式的作用下,“哈戎”仪式象征含义通过“另类交融”得以表达;第四章解读了“哈戎”仪式场域中的象征结构与象征符号。“哈戎”仪式的象征结构主要有“二元、叁元、五元”叁种基本类型,这些结构都是一种深层次的“无意识”结构。支配性象征符号和工具性象征符号是“哈戎”仪式场域中两种主要的象征符号类型,这些象征符号具有“浓缩”和“多意”的结构属性,是仪式象征意义的“介质”和“载体”,承载着纷繁复杂的深层的文化意义。总体来看,全文是在对亻革家人“哈戎”仪式操演的民族志叙述的基础上,从“主导象征—过程象征—象征结构—象征符号”四个方面建构起了“哈戎”仪式的象征网络系统,通过对这一特殊的象征网络系统的研究,我们阐释出了亻革家人在“哈戎”仪式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李四玉[5]2017年在《纳西族传统东巴婚俗现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纳西族的婚俗文化与其社会形态、经济结构、东巴教信仰、婚姻制度息息相关。基于文献参考和玉龙县新主村纳西族传统东巴婚俗的田野调查,认为传统东巴婚俗具有鲜明的民族宗教特征,复杂的地域差异,独特的时段差异的特点,并且具有历史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要采取加强科学研究,提高社会传承意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保护与发展结合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象征与意义:叶青村纳西族宗教仪式研究[D]. 鲍江.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2]. 《象征的来历: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序[J]. 和少英.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09
[3]. 民间文化遗产传承的原生性与新生性[D]. 冯莉. 天津大学. 2012
[4]. 祖先之荫庇[D]. 李技文. 中南民族大学. 2011
[5]. 纳西族传统东巴婚俗现状研究[J]. 李四玉.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