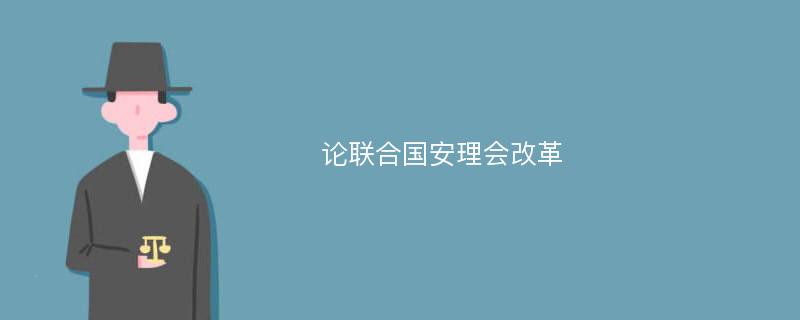
王志琛[1]2016年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的中俄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时期,苏联把联合国当成同西方国家斗争的舞台,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联合国外交才发生改变;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后,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不仅反对美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俄面临相似的战略环境,双方逐渐加强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安理会是中俄在联合国框架内合作最重要的机构,双方在安理会中的投票凝聚力指数保持了长达十五年(1995~2009)的高水平,2010年后有所下降。朝鲜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是中俄合作取得较大成果的两个案例,中俄连续叁在安理会中否决西方国家关于叙利亚的草案,是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联合国中的具体表现。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卓有成效的合作,不仅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同时维护了联合国的权威,还保障了中俄自身的国家利益,双方将继续加强在安理会改革、“保护的责任”等问题上的务实合作。
高笋元[2]2006年在《大国权力角逐下的21世纪初安理会改革研究》文中指出纵观世界历史,我们的世界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在国际政治发展进程中,大国主宰国际政治格局的历史事实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大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彼此间时常为争夺权力而角逐,虽然权力角逐的方式从以直接战争方式发展到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大转变,但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大国之间的这种权力角逐并未趋于明显减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也正是基于大国主宰国际政治格局这一历史现实,在文中作者首先分析联合国安理会是在大国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然后进一步探讨了安理会改革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动因,从而说明安理会改革是五大常任理事国、新兴大国间为了自身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展开的一场权力角逐,这也就决定安理会改革必将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无论安理会改革的进展如何,只要这一机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安理会就摆脱不了大国在其中所占据的领导地位和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因此,面对大国主宰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作为一个在安理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享有特权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来说,在当前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应该采取更为务实、灵活而有效的斗争策略来维护中国在安理会的大国权力和地位,以便使中国能够在未来的国际权力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铺平道路。
周海峰[3]2008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着重系统考察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对联合国改革的政策及其异同,并对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和美国的联合国改革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联合国改革所面临的机遇和困难,把握联合国改革的发展走向。冷战结束之后,面对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国际格局的转变,联合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再加上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和安南都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的进程。联合国改革既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和围绕建立何种国际秩序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某种理想主义的体现。拥有强大“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美国在联合国改革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其政策深深影响着联合国改革的进程。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改革联合国的呼声以及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提出了对联合国改革的政策主张。这两届政府的政策主张虽存在着差异,但更多的还是两者的一致性。对联合国改革的态度和所强调的改革的重点是两届政府政策的差异之处,但给予联合国在行政与财政方面和安全与人权领域改革以高度关注,而对安理会改革和发展领域改革的漠视,以及政策主张中所体现出的实用主义,则是两届政府政策主张的相同之处。造成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联合国改革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会和两党政治的影响、两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认定的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威胁的重点以及两届政府外交理念的不同,而美国的单极霸权战略、制度霸权、对联合国的定位以及“美国例外论”是两届政府政策一致性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我们分析美国政策的最主要出发点。美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联合国改革的主要议程或走向,它既是联合国改革的“助推器”,又是联合国改革的“绊脚石”。对于维护美国的霸权来说,它的联合国改革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美国政策中的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也使美国的声誉和霸权的合法性受到损害。因而,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一种权力与权威的关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政策主要来源于其“软权力”,但在其推行过程中却损害了其“软权力”。同时,联合国的改革则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联合国及其改革中所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这也就需要美国实行必要的自我约束,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对待联合国及其改革。
李浩民[4]2013年在《论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性及否决权的改革》文中提出全球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风起云涌,全球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就对联合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联合国核心机构的安理会,是联合国改革的重点。纵观各方提出的改革方案,对于安理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是安理会的代表性和否决权的改革。本文主要也是对这两方面的改革进行探讨。
周小跃[5]2011年在《冷战后中美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政策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自联合国创建以来,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有关其争议也一直不断。特别是冷战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是安理会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中美作为安理会内重要影响的常任理事国和世界性大国,其对待改革的政策和立场,自然重要而耐人寻味。本文首先从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历史脉络梳理开始,阐述安理会改革涉及的问题、一般事实及改革的原因分析。第二章,分别阐述了中美两国关于安理会改革的政策,其中重点阐述了冷战后中美关于安理会改革的相关政策,为引出后一章的政策对比作铺垫。第叁章,在安理会改革相关概念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中美可行性,从两国政策演变对比及特点两方面入手,对两国政策变化及特点作了系统的比较,并分析其背后的成因。第四章,以2005年中美安理会改革问题政策为例,从文本分析,政策理论基础,和战略对比叁方面,说明前一章的对比分析。第五章,在前一章基础上,对美国政策提出预测,对中国相关政策提出建议。最后,回顾总结前五章内容,升华主旨。
张芹芹[6]2010年在《冷战后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联合国作用的不断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重要。同时,联合国日益受到全球性问题的挑战,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任务。安理会作为联合国中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机构,其改革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许多成员国认为安理会已越来越不能反映当今的现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理会缺乏广泛的代表性。1945年联合国刚成立时,安理会虽只有11个理事国,但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和的20%;1963年联合国会员国增加到113个,安理会理事国增加到15个,约占会员国总数的12%;而今天联合国会员国总数已达192个,按比例只占将近8%。二是安理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冷战时期,美苏利用否决权轮番控制安理会,使安理会几乎瘫痪。因此,冷战结束后,人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安理会进行改革。各大国家和集团纷纷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提出的各种关于安理会扩大的方案,如拉扎利方案、名人小组报告、四国联盟方案等。但是,方案虽多,由于种种原因各国互不退让,针锋相对,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迄今仍未达成一致。事实上,在安理会改革中,美国的态度和政策是举足轻重的,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力量是任何国家都无法超越的。从美国近年来的立场与运用的种种策略手段可以看出,美国对安理会改革兴趣索然,对安理会的扩大更是态度消极,对否决权的扩大则毫不含糊地坚决反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则积极支持安理会改革。其实,对改革最热心的国家应属德国和日本。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德日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国际上的经济大国。它们希望能尽早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从而获得政治大国地位。然而,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方案能够获得各成员国的一致通过。安理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更多国家的利益,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因此,安理会改革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世界各国希求和平与进步的人们希望安理会改革能够早日取得成功,也希望改革后的安理会更加民主、更具有代表性、更为高效。
魏娟[7]2007年在《不平坦的日本争常之路》文中指出日本在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后,开始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家组织,在协调国际事务和开展国际活动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成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最佳途径。而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的展开,为日本争常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为实现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日本一直进行多方努力,积极为联合国各机构出资,增加会费比重,参加维和活动,参加联合国名义下的各项活动,争取各会员国的支持。2005年,日本再次为实现这个目标展开活动。为增大入常的可能性,日本与德国、印度、巴西结盟,采取“捆绑式”争常的政策,但是此次行动仍然没有成功。各会员国对日本的争常反应不一,日本尚未能取得多数支持。而日本国内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安理会改革本身的复杂性也都成为日本争常路上的障碍。日本能否实现其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既取决于日本自身条件,也取决于各会员国对日本的认同程度和安理会改革的进程。在当前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下,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在短期内还很难实现。
刘军华[8]2003年在《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文中研究说明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改革中最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部分,关系到联合国的生存和发展。当前安理会改革的重心在安理会的决策机制、组成结构和运作机制叁个方面,涉及组成的扩大、否决权和民主化叁大问题。 否决权制度本身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而且某些常任理事国大肆滥用否决权,严重阻碍了安理会顺利地发挥作用,否决权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否决权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现在否决权依然是联合国生存的基础和支柱,是大国矛盾的缓冲器,因此否决权不能取消,但是必须对否决权加以限制,以减少其消极作用。 在安理会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过小,地域分配也不合理,许多国家提出各种改革建议。安理会改革应当要提高安理会的效力和效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名额,同时也要吸收一些强国进入,新增常任理事国不应拥有否决权。 安理会的“非正式磋商”不利于其他会员国充分参与决策,必须增加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安理会应经常向大会提交详实的报告,尽量让其他会员国充分参与安理会的讨论和决策。但是五大国的内部磋商不能取消。 安理会改革实际上是各方在联合国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安理会改革必须坚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循协商一致等原则。安理会改革对中国利益的影响是利弊兼有,中国一直支持安理会改革平稳进行。由于美国的霸权战略和安理会内部存在的问题,安理会改革在短期内还不会有重大突破,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安理会改革有望取得重大进展。
李涛[9]2009年在《新世纪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其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国际社会民主化、有序化观念深入人心,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这些都对联合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联合国机制至今还基本上维持着五十年前的设计,不能反映新的国际力量对比,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实在难负重任。联合国完成历史使命的关键是进行改革。国际社会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联合国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联合国6大机构中为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而行使决策权力的核心机构,是联合国集体安全的象征,在安理会成立以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地区冲突作出了独特贡献.安理会的改革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的改革以及整个国际秩序的变化,本文以联合国安理会的新世纪改革为切入点,阐述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从不同方面分析研究各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进而研究和阐明这一世界最大国际组织改革的现实意义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导引出新时期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以及改革所面临的一些重大而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二部分系统论述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宗旨及方案,以及国际社会各方对于安理会改革的不同态度。第叁部分分析了当下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面临的一系列制度性挑战和现实困境。最后部分是结语,总结全文的基本论点和主张,对今后的联合国改革进行了展望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赵磊[10]200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运用主流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所提出的核心理论假设是: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实践形成了文化结构,即共有观念,特定的文化结构建构了中国的身份、利益和外交政策。研究过程中,论文将建构主义与层次分析方法结合,力图从“国际体系”、“行为体间”及“行为体内部”不同层面来全面分析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文化结构因素。此外,在静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创立了研究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动态演进模型,以期提供分析、预测外交行为的简单量化方法。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将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分为叁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949-1971年,中国将主权利益作为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第二阶段是1972-1989年,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走上正常轨道,发展利益成为中国考虑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指标;第叁阶段是1990-2004年,中国与联合国友好相处,以负责任的心态重视对联合国各方面行为的总体考量。在经验验证部分,文本指出,50、60年代,中国与联合国互动起点始于朝鲜战争。此后,双方互视为敌人。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定位下,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是挑战;在美国间谍案、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中国代表权等问题上与联合国针锋相对。70、80年代,各层次文化结构逐渐缓和,中国与联合国走上“正常化”道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工具性”视角审视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进入90年代,中国与联合国在“规范合作”基础上,形成了助益双方的“制度性环境”;在联合国“正面激励”作用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主动建构与联合国的“集体认同”。在案例验证部分,本文证实,观念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对维和行动的行为特色。“稳步推进”由“参与者”上升为“引导者”是未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行为趋向。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的中俄合作研究[D]. 王志琛. 黑龙江大学. 2016
[2]. 大国权力角逐下的21世纪初安理会改革研究[D]. 高笋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3].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政策研究[D]. 周海峰.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4]. 论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性及否决权的改革[J]. 李浩民.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5]. 冷战后中美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政策之比较研究[D]. 周小跃. 外交学院. 2011
[6]. 冷战后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研究[D]. 张芹芹. 青岛大学. 2010
[7]. 不平坦的日本争常之路[D]. 魏娟.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8]. 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D]. 刘军华. 湘潭大学. 2003
[9]. 新世纪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探析[D]. 李涛. 新疆大学. 2009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D]. 赵磊. 外交学院. 2006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论文; 中国重返联合国论文; 联合国秘书长论文; 联合国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